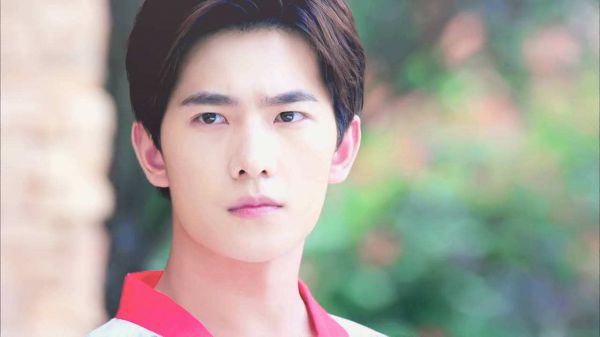去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颁给了匈牙利影片《索尔之子》,本片的剧情很简单,一句话概括: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特遣队员索尔,在“工作”中发现经过毒气处理却未立即死亡的“儿子”,早已麻木的索尔引为神迹,决心在这必死之地,做最后的对生的希望的寻觅——找个犹太教士,为“儿子”以犹太教方式下葬。
索尔之子的主线剧情,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死中求生的故事。电影的副线,同样如此:必死之身的特遣队员们串联起来,想要逃出生天。主线与副线的连接点,就是索尔,他在副线中的任务,是与女特遣队中的妻子接头,获得弹药,以作反抗之用。但索尔的心思,在主线,不在副线,他一门心思的想要找到犹太教士,甚至利用自己在副线中的重要性,最后在寻找教士的过程中丢失了弹药,葬送了特遣队员们最后反抗求生的机会。
显然,副线的求生,是实实在在的求生,是实。主线索尔的求生,是精神层面的求生,是虚,为了虚的求生葬送了实的求生,到底值不值得?这也是观众对本片叙事逻辑、索尔做法最大的一个争议点。但在索尔那里,很坚定,他自始至终没有对自己的求生信念产生过动摇。
对此争议点无法给出定论,但却知道,这虚,也很重要,即便是在中国。一个人活一生,也许就是这个虚,才是最让他快乐的,即便不是在奥斯维辛。今年刘雨霖把她爸爸刘震云被称为近十多年来最“有意思”的小说搬上了大银幕。电影中的故事,讲的是牛爱国。小说大部分篇幅,讲的其实是杨百顺。杨百顺一生最喜欢的,是喊丧的罗长礼。罗长礼的主业是种菜,喊丧只是他的兼职。杨百顺喜欢的,是喊丧的罗长礼,而不是种菜的罗长礼。杨百顺这一生喜欢的,就是罗长礼在人世间的这一“喊”,杨百顺这种情况,在河南老辈中,叫做“虚”。世界上精神层面的东西,无论宗教与否,大体相同,为儿子寻找犹太教士下葬,求生的索尔,就像这一生只喜欢那一喊的杨百顺,这个“虚”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不然活的没意思,对索尔来说,连死的都没意思。
本片的导演,拉斯洛•杰莱斯是认同这虚的重要性的,不然也不会拍这样一部电影。他甚至在上面所说的争议点上,有自己情绪的倾向性,虽然没有表达在影片中;他是认为在奥斯维辛,谈“生”(实实在在的生)是残酷的,残忍的,“不对”的。然而许多表现犹太人这场灾难的电影,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几部,却都是在谈生——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美丽人生等等。拉斯洛想做的,是拍“死”,一切都是“死”。特遣队员们,包括索尔,他们的求生经历,都是在一片“死”中度过的,可以说镜头的真正落脚点,不是带着死气实则暂时活生生的索尔的脸颊,而是虚焦中的那些东西:毒气室、解剖室、尸体、骨灰堆等等等等。
小伙伴们如果知道这句话,看完电影肯定会想起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野蛮的,这是定论。意淫一下如今的创作者们,在舒适的环境中一厢情愿的模拟浩劫的一切,就更加确定这种野蛮了。然而肥哥的观点却是,这种野蛮,如果不纯粹是商业化的行为,是需要继续下去的。因为如果说没有了文字、影像等等对灾难的重塑,提醒,人类是会渐渐模糊,甚至忘记的。这种忘记,更加的野蛮。
因为这种野蛮,拉斯洛在本片的融资过程中就遇到了重重阻难。当然,有多少犹太人想要去回忆这场惨痛浩劫,有多少其他人想要看一部辛德勒、浩劫、钢琴家等等影片之外的集中营影片,也是拉斯洛遇到困难的原因之一。虽然拉斯洛有着很好的个人资历——其几部短片在诸大电影节的获奖等等,但题材的问题,注定了这位野心勃勃的长片处女导演在资金上的困难。然而拉斯洛找到了一条好路,既省钱,又有开创性,他让摄影师扛着摄影机一直跟拍暴走的索尔的头部,传统的景深中的内容变得模糊不清,却未减少一点其内容的丰富性,反而有所加强。可以说拉斯洛的这场镜头实验,完成的堪称完美,与电影要讲的故事,想要传达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切,配合的天衣无缝。这种野蛮,也许已经是最好的野蛮了。
喜欢这部奥斯卡外语获奖片,看的过程中不只觉得特别,游戏第三人称视角式的代入感也很强。去年最后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五部电影,还有来自丹麦的《战争》,来自约旦的《希布》,来自哥伦比亚的《蛇之拥抱》,以及来自法国的《野马》。最终奥斯卡选择了这部关于奥斯维辛的影片。奥斯卡有时会垂青与纳粹有关的影片,仅只新世纪就有四部最佳外语片与纳粹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每年的提名影片中,更是屡见不鲜。奥斯卡有时会排斥这种重复,却又时不时的给予肯定。欧洲这场“浩劫”的创痛,还会在电影中延续很多年,且看之后奥斯卡的选择吧。
16年中国三地的选送影片分别是,内地是《滚蛋吧肿瘤君》,这电影看看乐呵乐呵感动感动也就可以了,没想到选片委员会当真了。台湾是《聂隐娘》,大爱侯孝贤没得说,但是得戛纳有可能,得奥斯卡几率太低。香港是《破风》。
这已经是匈牙利第二次摘得此奖,上次是1982年的《梅菲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