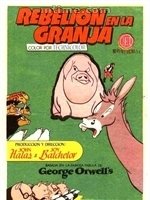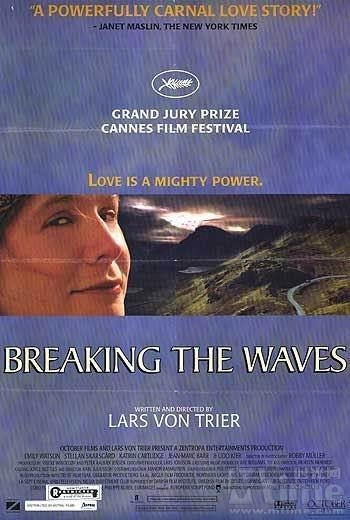我们的电影人物不感人,一直是一个附着在某种概念下的纸片生命体。英雄就是毫无人性地好,坏人倒是偶尔可以坏出一两个层次。
在我们的电影里,人服务于概念,服从于集体。而概念和集体从来都是工具性的,工具的生命,从来都是单调、重复的。
我们的电影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旦发现了某个真相,就会臣服于这个真相。我们比巴普洛夫的狗还忠诚地,去维护这个真相的唯一性。
我们习惯于扎尔伯格创建,是一种成功的《社交网络》模型,就很难从泡妞失败这个角度去打量事件,我们甚至也不敢去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打量事件。
我们强调的是集体,一种概念,一种大而无形的东西,我们失去了对人的兴趣,也失去了观察和呈现人的能力。
我们的创作者习惯了标准答案,故事失去了丰富的可能。从小我们就习惯了在一段文字中寻找中心思想,而这些中心思想是被若干词汇,以踩分点的形式规划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