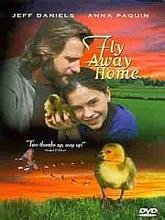《路边野餐》发生在导演的故乡、潮湿神秘的贵州黔东南,按照人物的时间线和电影的故事线其实我能给出两个版本的情节,不过这里糅在一块说,抱歉要严重剧透了。主人公陈升是个曾经混过黑社会的乡镇医生。大哥“花和尚”的儿子因为赌债被人砍手并活埋,于是他前去讨公道,并且因此坐了几年牢。出狱前他的妻子也过世了。而花和尚的儿子不断托梦给父亲,让花和尚烧手表给他,后来花和尚在镇远改做了钟表匠。陈升小时候被寄养在附近的城市,因此母亲觉得对陈升有所亏欠,帮他找了乡镇医生的位置,并在过世前将房子留给了陈升,但陈升还是没出现在母亲的葬礼。房子和送终的摩擦也令他和母亲一手养大的弟弟心生龃龉。陈升的弟弟是个单身父亲,但对儿子卫卫不怎么负责,常把他锁在家中自己出去玩。因为对母亲的复杂情绪,陈升常常来看望卫卫。收音机里说,9年前出没的野人最近又有所活动,卫卫很害怕。误以为卫卫被卖掉后(实际是花和尚听说陈升弟弟要卖儿子,就将卫卫接去镇远),陈升计划去镇远找他。诊所的同事是个老太太,她托陈升将自己的信物带给住在镇远的旧情人,于是陈升带著一张照片、一盒磁带(李泰祥和唐晓诗的《告别》)和一件衣服来到了荡麦。
在荡麦,导演开始了那段最为人称道的四十多分钟的长镜头。陈升坐上一个也叫卫卫的青年的摩托车,前去找老医生的情人——一个会唱歌的苗人。没找到人又想赶在天黑前到镇远的陈升,搭上了一只乐队的顺风车,乐队正要去另一个寨子表演,陈升说自己不会唱歌只听过儿歌,于是在车上乐队播了童谣《小茉莉》。在一个路口陈升看到刚刚搭载自己的卫卫站在塑料桶里,头上倒扣着塑料桶,于是下车帮他取下,原来是其他开摩的的年轻人想抢卫卫手里的望远镜故而捉弄他,卫卫顺手将望远镜递给了陈升。陈升帮卫卫修好了不停熄火的摩托车,让卫卫将自己送到去镇远的码头,并先跟着卫卫来到临近的一个寨子。导演对长镜头的准确设计和长镜头呈现复杂空间结构的优势在这一段展露无疑,黔西南的村寨不少依山傍水,木质房屋也沿斜坡而建,中间穿插着逶迤盘杂的小道。镜头快速从一段长台阶下移,刚才紧贴着的摩托车声也由近而远由远而近。等镜头来到台阶下的另一片空间,卫卫的摩托车刚好开到。镜头继续紧贴着二人,先去吃了碗粉,再去缝补陈升掉了纽扣的衣服。在这一段,毕赣本人还穿着汗衫打了个酱油。
给陈升补衣服的裁缝洋洋是卫卫的心上人,她很快要去凯里做导游,正在勤背导游词,“凯里位于贵州东南,最高气温xxx,最低气温xxx”。隔壁理发店的女孩来找洋洋看演出——刚才陈升搭便车的乐队晚上要在这里演出,陈升换上了老医生的花衬衫,去找理发店女孩洗头发。另一边洋洋一个人沿着台阶走到河边,边背导游词边坐着摆渡船到对岸,买了个花里胡哨的手风车后,卫卫追赶上洋洋但她爱理不理,河对岸隐约传来乐队开始演出的声音,两人又沿着吊桥走回了对岸。这里理发店的女孩正在帮陈升洗头,陈升以第三人称讲起了自己和妻子的故事。而观众会发现,理发店女孩和前半部分曾经一闪而过的陈升妻子长得一模一样。陈升、理发店女孩、卫卫和洋洋一起来看演出,乐队疑似唱了《公路之歌》后(记不清是排练还是演出时唱的),陈升走上前说自己想唱一首歌献给理发店女孩,于是磕磕绊绊地唱了刚才听来的《小茉莉》。唱完歌,卫卫告诉陈升得要走了,将刚才做的手风车送给洋洋,而陈升掏出本来要带给老医生情人的磁带,送给理发店女孩。两人坐着摩托车离开,卫卫告诉陈升,自己在与前去凯里的火车方向相反的货运列车上用粉笔画了很多时钟,两辆车相遇时,看上去时钟就在倒转。卫卫还告诉陈升,最近野人出没,让他在手肘上绑两个木棍,这样野人扑来时不会猝不及防。直到这时长镜头才结束。陈升在镇远路边的钟表车找到花和尚,花和尚说起卫卫学校的手工课要买纽扣,又让陈升不用担心,开学了就把卫卫送回凯里。陈升将一把纽扣扔进花和尚的车里,拿起望远镜远远看了卫卫一眼,然后离开了。老医生的情人已经过世,陈升将花衬衣和照片交给苗人的儿子,说磁带在路上遗失,接着回到了凯里。两列火车相遇时,陈升看到了倒流的时间。影片最后一幕是一列消失在隧道的火车。影片进行了四五十分钟,才出现了片头《路边野餐》。上述这些情节,大多并未直接出现在片中,而是透过人物对话和回忆拼凑,伏笔非常细密,不少内容我第二次看时才留意。因为画面中现实与回忆交错、加上诗歌的运用,所以真实的情节颇有些梦幻感;而发生在荡麦的颇有些魔幻感的情节(遇到叫卫卫的青年、与妻子长相一模一样的女人、与9年前野人的对应),因为一镜到底的完整脉络和叙事,反而给人更真实的感觉。
片中陈升的另一重身份设定是“蹩脚诗人”,操着当地方言念出的诗歌旁白,在不少情节和画面起到间离效果和并带来超现实感,也与影像内容有些似是而非的对应。印象较深的一处诗歌旁白是,陈升怀疑弟弟把卫卫卖了,去打牌的地方找他,两人一语不合打起来,这时镜头扫过地上的一滩水,影片出现陈升念的诗歌和字幕;镜头这摊水扫过,陈升在同一处地方与人起争执,但从对话中我们知道,这是9年前陈升找砍掉花和尚儿子手臂的人算账。前半部分的时间切换全在不经意间,但导演依然通过诗歌、对话、甚至影片色调留下一些提示。又比如陈升昔日兄弟将他从看守所接出来的画面,印象中色调比之前偏暗黄。如果想要捕捉全部的情节,第一遍看《路边野餐》会非常吃力,因为观影前半段对情节没什么头绪,渐渐意识到故事梗概时又会错过一些伏笔。比如上文提到的,陈升搭乐队顺风车遇到青年卫卫,卫卫顺手递给他一副望远镜,后文陈升看小卫卫时用的正是望远镜;又如陈升扔给花和尚的纽扣,正是在洋洋处缝补后剩下的;又如陈升洗头时,习惯性背着的手(监狱待太久留下的习惯);又如青年卫卫提到自己在货车上画时钟,火车开过时不留意看很容易错过,而时间倒流的画面电影前半部分还出现过一次,那是小卫卫在自家墙壁上画的时钟,时钟中心有一颗钉子,投射在墙壁上的指针实际是钉子的倒影,所以它的移动方向也是反的;又比如理解陈升对理发店女孩的一见钟情,需要记得电影前半部分一闪而过的画面中的他的妻子的相貌。但对情节的一知半解某程度上并不影响观影。《路边野餐》兼有聪明与笨拙的气质,这种聪明指的是精巧的结构设计,包括种种伏笔、对应、信息量丰富又运用从容的长镜头(喜欢长镜头对几个空间的同时收纳,比如跟着洋洋渡河的时候我能隐约知道乐队在调音、陈升在洗头、寨子里的一切都照着自己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推进着),而这种笨拙则是人的情感本能。洋洋渡河时背导演词卡壳,卫卫在河的另一边故意大声念出,洋洋带着窃窃的欢喜勉强自己不去听,上岸买手风车又赌气走开这类小儿女情态是很迷人微妙的;陈升对侄儿卫卫、对妻子(体现在理发店女孩)、包括对母亲的情感,是尤其属于一个中年男性的无所适从与笨拙热烈。野人传说的时态变化(9年前,最近)所指向的时间穿越,和梦境般的体验(亲人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进一步化解了直接面对情感的尴尬,也更符合写诗的乡下医生这样看似粗糙实则内心细腻的人设。正如导演说过的一句话,“电影是假的,情感是真的。”
今天几乎怀着朝圣的心情去看了!现在有点庆幸我在一线城市过暑假了,很多想看的朋友都苦于没有排片,今天这场上座率有百分之五十,算是不错了,观众都很有素质,期间大家几乎都没有打开手机看时间也没有接电话什么的,好像所有人都被毕赣带进了陈升的过往。说一个东西吧,火车,这个东西很神奇,在贾樟柯的电影站台里,崔明亮一行人追着火车跑的镜头我想看过的都不会忘记,路边野餐是主讲陈升,可我对洋洋和另一个卫卫这种年轻人有很深的感触,洋洋听见火车声的那一刹那眼里好像有光,她在听说老陈是从凯里来的时候也换成了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她努力装扮自己,对卫卫的追求视而不见,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属于这里,她想出去,这是年轻人,想往前走。再来说老陈,我在湖南上大学,去过镇远,毕赣最神奇的就是他在电影一开始就把我带进了回忆里,我在电影院吹空调可我莫名觉得周围的空气都是潮湿的,梦回南方好魔幻现实主义。陈升,没有母爱地长大,坐牢9年和妻子离婚,妻子逝去2年才知道,兄弟不和,其实内心很渴望爱,我觉得是更偏重于爱别人。他的诗用了动物还有自然界的现象,忧郁怅然,从里面我听出了遗憾,遗憾没有陪伴母亲,遗憾自己的妻子,过往云烟虽已飘走,可他依旧是想抓住一些东西,所以他想要照顾卫卫,愤怒母亲的墓碑上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于妻子的离世,这也说明了他什么也抓不住。就像老医生,爱人已仙逝。镜头很干净,最喜欢的一个镜头是墙上映出火车,很魔幻,然后还有很多镜中镜的镜头,很有意思。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做Kaili Blue。我更喜欢这个名字。去看吧,总会有什么收获的。
《路边野餐》谈论的是失去。失去挚爱。失去年华。失去希望。失去活下去的理由。当然,自打我们生下来,我们就一直活在失去之中。可是,有些失去可以习以为常,有些不能。那些失去,需要出口,去表达。不必多说,点到即可。陈升失去了妻子,老年女医生和花和尚失去了各自的儿子,老歪失去了生活和卫卫。然而没有人去谈论失去,正如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那样——没有人把失去挂在嘴上。那些失去化作淡淡的影子,沁在生活的这块越来越浑浊的画布上,被收藏进老皮箱里。偶尔拿出来看,往事触目惊心。所以陈升需要一场酣畅淋漓、春意盎然、绿莹莹的长梦,在梦里,卫卫长成一个可爱的小伙子,还有了喜欢的姑娘,病逝的妻子在理发店里安安静静地做着生意,眉眼恬淡,美丽依旧。陈升高兴起来,站到话筒前面唱了一首在牢里唯一学会的歌曲,儿歌,《小茉莉》。美好的梦。但愿长梦不愿醒。我们每天都需要八个小时足足的睡眠,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梦,把我们带向远方,带向爱人,带向诗意的生活。缺了梦,谁都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