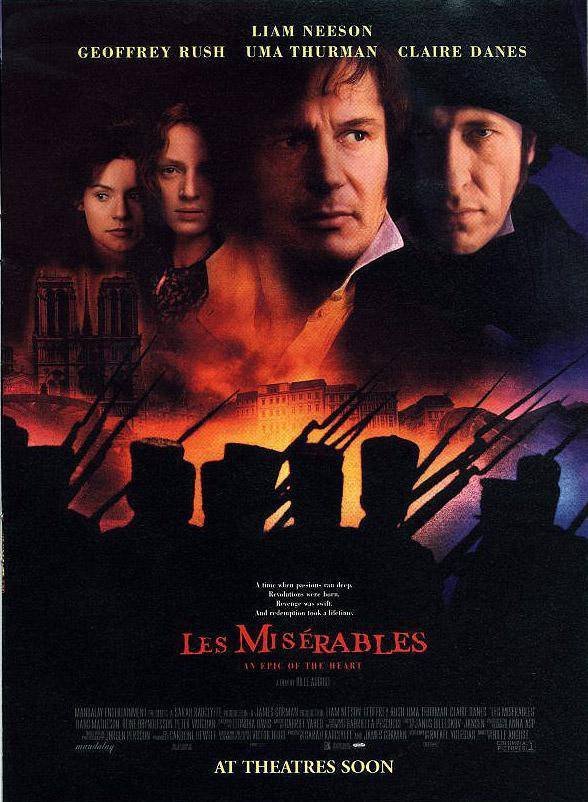汉人还是一个温顺、尚文、逆来顺受多于揭竿而起的民族。所以,当身为汉人的魏德胜导演,忽然从文艺到死且充满了“殖民”风情的《海角七号》,转身宣布《赛德克.巴莱》的拍摄计划时,我们除了期待,还有惊愕。
无论对本片抱以怎样的态度,我们都不得不向魏德圣对电影的热爱致以崇高的敬意。《海角七号》大卖带来的数千万新台币盈余,被他毫不犹豫的投入新片拍摄之中,而结果哪怕如同有人计算的那样基本持平,这数千万于他也彻彻底底的成为了没能在钱袋里捂热的过路财富。更不要说如果导演本人声称的尚有亏损属实,那么这部电影的拍摄,对于魏德圣来说,更是成为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虽然电影以台湾日据时期的“雾社事件”为背景,但整个电影的主题,却并非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压迫与反抗。事实上,汉人在本片之中占据的戏份非常之小,而偶尔出场的几个汉人,也多是欺软怕硬、卑躬屈膝,形象气质尽皆猥琐,莫道比不上英勇的赛德克人,就连充当反面人物的日本军队与警察,也远远赛过。
这部影片,描述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是人性与兽性的对决,是一种信仰与另一种信仰的对弈,甚至,是历史潮流与反历史潮流,现代进程与反现代进程的对垒。 但是,无论野蛮也好,兽性也罢,在这里却并非贬义词。这些充满原始力量的词语,其包含和反馈的,正是我们汉族所缺少的阳刚与血性,是充满生命力和自然法则的率真品质。纵使历史潮流和现代进程是不可逆的,那一群群以卵击石的赛德克.巴莱们也为世人展示了,人性中最原始的野蛮力量,有着怎样的伟大与不甘。
从日本入侵台湾肇始,整个剧情像一根渐渐拉紧的橡皮筋,既充满压抑和不安,又不断聚集着等待爆发的张力。莫那鲁道从年轻时的抵死反抗,到中年后的成日买醉装聋作哑,整个赛德克族从如同野兽般主动出击,到如同家畜般忍辱偷生,似乎一种野性和力量正在悄然消逝。可是头人偷偷积攒的火柴磷粉,和年轻族人们面对日本人时充满愤怒的眼神及面对“归化”同胞时的不屑与嘲弄,又分明在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掀起涌动的暗流。
在婚礼的受辱与反抗后,盗火线终于被点燃,被压抑了数十年的满腔愤怒,让赛德克人选择了将仇人送上祖灵的血色祭坛。与其说那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一场血淋淋的杀戮。而这,也引发了整部影片最大的争议。无论如何,针对平民的军事行动,也应该被归入恐怖主义的范畴,对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举起屠刀,更是无论古今中外的道德观都不能允许的事情。
但导演并没有刻意去回避和美化在“雾社事件”中所发生的这些罪行。虽然少年巴万将屠刀挥向无辜日本妇孺的镜头被做了出画处理,避免一些过于血腥和让人不快的情节直接出现,可谁都清楚,这样的事件无论在电影里,还是在当年的史实中,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却并不会像憎恶现实生活中的ISIS那样毫无人性的凶手一样,去憎恨这些掀起腥风血雨的“生番”,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随着观众逐渐沉溺剧情之中,不自觉的将自我感情带入作为影片正面描写的赛德克族一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所有沾满鲜血的屠夫们,最后都以英勇战死或是自尽身亡的方式,为自己进行了彻底的赎罪。
探讨国民劣根性的文章,大概很少有谁能像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那样振聋发聩。无可否认,我们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有着足以让每一位炎黄子孙骄傲自豪的历史和文明。但同样的,这个民族也有着无可回避的缺点。无论是从远古农耕文明一点一滴形成的也好,在崖山之战后被异族统治所扭曲的也罢,华夏人民集体性格中的糟粕,已经成为血脉和基因中的一部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人有能力改变。
比如尚武精神、阳刚血性的缺失。诚然,华夏民族千年苦难史里,也有将星辈出,英雄如云的时代,但从全体国民的层面来看,却更多的是浑浑噩噩等着人血馒头治病的无知民众,围观为俄国做间谍的同胞被日本斩首的麻木百姓。所以,第一批走进初开国门的大清帝国的西方人,留下了这样的话语: “这个帝国的百姓毫无生气,神情呆滞与麻木,他们穿的破破烂烂,如乞丐一样。”
信仰、理念,热血、奋斗,这些美好的词语,似乎在中华大地被异族统治的几百年间,随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沾满鲜血的过往而一齐消逝,只剩些摇头晃脑的八股书痴,和埋头过活的温顺良民。
而后的爱国救亡、西学东渐,随着政权的次次更迭,一批批国民觉醒。而国家危亡之际的绝地反击,也让这个民族最后的血性全盘爆发。可以说,正是一次次危急存亡之秋,为我们的民族找回了一些千百年前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