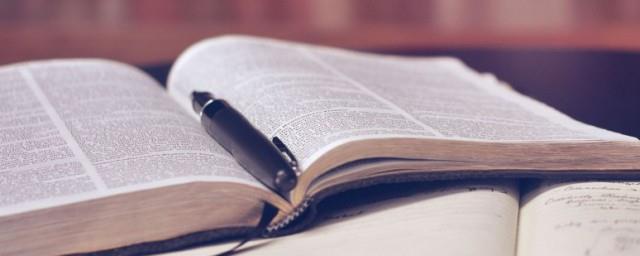本片一女两男的设定很难不让人回忆起有女权意识的《朱尔与吉姆》,然而本片的男女主角性格走向却不如后者生动敏锐。三个无所事事却又渴望大有作为的男女策划了一场抢劫,他们是社会、群体、政治、法律、道德的圈外人,带着对一切失望透顶又不屑一顾的漠然,没有目的性的随性生活。看到最后才知道王家卫的“无脚鸟”出自这里,出现在在阿瑟死时的画外音:他看到印第安神话中的奇鸟,他生来没有翅膀,永远不能落在地上,它御风而起,只有临死的人才能看到那比鹰还长的透明翅膀,慢慢合上时,变得比手还小。
在新浪潮电影革命里,对人情感和内心的关注排在首位。周围的物事都是为了展现人物内在需要,大量隐晦的暗喻和放纵出现在观众眼前,既没有面临战争的坚定信仰、也不似时代发展寻求突破的变革,这个时期是尴尬的、是感性的。太过于关注内心会使脆弱的人加速灭亡,任由自我流亡到远方则会格外痛恨揭穿真相的电影。恐惧它的个性和标杆,恼怒它的深挖和尖锐。
女孩奥迪尔认识了男孩弗朗兹,在英语班上又通过男孩弗朗兹认识了他的死党阿瑟。奥迪尔告诉弗朗兹她住的地方有一大笔现金,弗朗兹告诉了阿瑟以及他的叔叔,所有人都在策划如何偷盗这笔钱。而真的到了计划实施的那天,不可逆转的悲剧和喜剧同时降临......
三个年轻人在小酒馆无所事事时玩起了沉默一分钟的游戏,在游戏开始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消音了,互相对视的男女似乎要被淹没在这片寂静中,渴望交谈却无话可说的哀伤使气氛逐渐变得诡异。在之后的跳舞中,音乐屡屡被冷静的画外音所取代,三个人脸上的欢乐和旁白中对各人心思的剖析形成鲜明的对比。到底是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梦,还是梦变成了整个世界呢。当人们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仿佛就将解救全世界的苦难作为使命。在最后的一场戏里,殴打和谋杀接二连三的发生,然而故事中的男女仿佛浑然不觉到底发生了什么。概念上的死亡仅仅预示着牢狱之灾的麻烦,而事实上他们额外得到的不义之财已经让原本不相爱的男女决定开始幸福的生活。明明什么都不在正轨上,却甜蜜的和所有普通情侣一样。
我最喜欢三个人在卢浮宫奔跑的一场戏,《戏梦巴黎》里也有向此致敬。狂放大胆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女在几百年历史的名作中狂奔,放肆大笑的三个人在或沉默或惊慌的人群中飞一般穿过,因为崇敬而来到卢浮宫却要用轻浮来对待它。因为矛盾所以热爱,性在傲慢粗俗中不再神秘,性情由内而外被暴露的彻底。明明想要抛弃整个世界,却只能以另一种手段融入其中。抓紧时间,美梦总是要醒,孤独才是永恒。
记得从一次昆汀的访谈中听到这样一句话:“梅尔维尔和莱昂内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重构大师。”说这句话的时候,昆汀应该不会忘掉戈达尔1964年的作品《法外之徒》,也是他从中受益匪浅的电影。
戈达尔对电影的了解自然毋庸置疑,只是如他一般学识渊博、博览众片的人要么成了有名的影评家,要么成了自成一派的导演,而戈达尔似乎一直以打破常规为荣,而甚少创立一种更易于大众接受的风格。《法外之徒》应该算是个例外,戈达尔借黑帮片的外衣,好不容易讲了一个简单而精彩的故事。说它简单,是因为影片只有3个主要人物,Odile,Franz和Arthur,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只有3个:教师、咖啡馆、Odile居住的别墅,而故事的情节发展,也是传统的3段式:起意——策划——抢劫。一切都是这样简洁明了,然而在三人之间却出现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景象,加上戈达尔如华尔兹一般的场面调度,简约中自有种轻松的美感。说它精彩,是因为即便在剧情暂缓之时,戈达尔也不忘用文字游戏、电影指涉和各种试验拍摄手法来插科打诨,在考验观众知识面的同时也幽了自己一默。就这样,90分钟绝无冷场,成为戈达尔最易理解的作品,同时又不失自己的独特风格。
影片另外一点给人启迪之处,就是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拍电影方式。有人说拍电影像调酒,而我觉得戈达尔拍《法外之徒》就像烹菜。美国黑色电影与低俗小说的刺激大餐,洒上法国文艺腔十足的甜蜜佐料,配着Michel Legrand醇美的华尔兹,还有戈达尔自己撰写的诗意旁白,这些看似毫不相干,几成俗套的陈词滥调,在戈达尔的调制下活力焕发,更融合成了一种全新又可口的口味,试问哪个痴迷电影的人会抗拒它的诱惑?30年后横空出世的《低俗小说》,其实亦是这番道理,所以昆汀除了那段兔兔舞之外,还从戈达尔那里偷师了许多。
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一件三人抢劫事件,但也夹杂着三角恋的情爱,容易想起同时期特吕弗的《祖与占》,特别是那场横穿卢浮宫那场,而《戏梦巴黎》同样有致敬桥段,而不少桥段更可看到其他后辈借鉴的范本,诸如间歇发作的旁白,有个连声音都抹掉的镜头都是戈达尔有趣的尝试,让这部略显黑色的电影内容丰富而玲珑活现。
总之,《法外之徒》让我看到了戈达尔的另一面。只要他愿意,他也可以像其他导演一样如玩游戏一般讲好一个故事,然而那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有时他也许玩火自焚,但那绝不是因为他玩不转火柴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