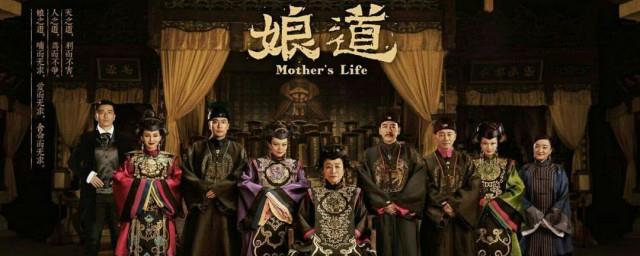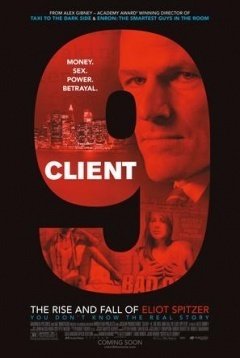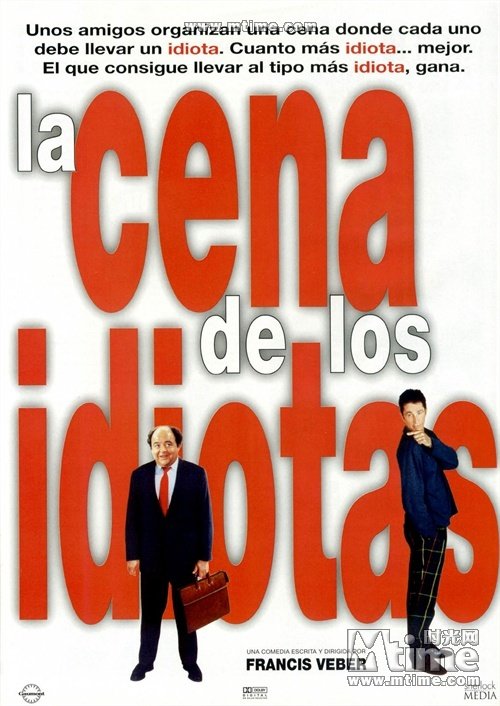对于贝多芬(1770-1827),我们似乎已经非常熟悉。辞世一百八十周年以来,贝多芬早已被公认是整个(西方)音乐史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伟人巨匠。汉语世界中对贝多芬的认识,可用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颇富文采的话语来作概括——所谓“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另一句解释贝多芬作品内涵的口号式箴言是——“从痛苦走向欢乐”,同样极富感召力。一般而论,我们好像满足于这样的界定,不再作深究。众所周知,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可被明确地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而人们最熟悉、上演频率最高的贝多芬作品是他的中期创作。音乐界已经达成共识,1802年之前可被看作是贝多芬的早期。此时的贝多芬虽已在维也纳显露才华,站稳脚跟,但创作内涵和风格尚显稚嫩。1802年至1803年间,贝多芬因患耳疾而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精神危机——他几近崩溃,并写下一份《海立根施塔特遗嘱》。令后人永远感佩不已的是,凭借艺术的力量贝多芬战胜了自我,并由此步入创作的成熟期:也即贝多芬的中期。而标志这场精神胜利的一个物质性结晶,就是那部极为著名的《第三交响曲》(“英雄”)。
自此至1812年,贝多芬在十年的时间中,创作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著名杰作。目前在音乐会中频繁亮相的贝多芬曲目,许多都出自这一时期:包括《“华尔斯坦”钢琴奏鸣曲》、《“热情”钢琴奏鸣曲》、《第五交响曲》(“命运”)、《第六交响曲》(“田园”)、《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三首》作品59、《小提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等等。这些作品不仅上演率极高,而且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强大影响。可以推断,鉴于贝多芬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即便他在42岁中年时就此辍笔,他也完全有资格成为整个音乐史中处于最高等级的大师之一。为此就不难理解,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中期风格的角度领会和认识贝多芬。总括而论,中期的贝多芬,典型地体现了“英雄”风格。在音乐技术上,贝多芬的追求集中体现为“扩展”:他全方位地开掘了当时音乐语言的各种潜能,具体做法如曲体上的大规模扩张,篇幅和长度的超常规扩充,主题/动机乐思的高密度运作,和声张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节奏冲力的高强度处理,等等。
在精神内涵上,这一时期的贝多芬创作,不妨用“人定胜天”这一成语来定位。需提请注意,这里的“人”,不仅指集体的人,更是特指个体的人。贝多芬的中期作品,明确体现出强烈的个人主动性和个人性的英雄主义,从而对人的积极力量作出了全面肯定。显而易见,这种带有强烈现代感的个人意识,正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遗产。贝多芬经由自己独特的个人(生平和艺术)体验,通过声音的特别方式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也就是为何我们后人每每听到贝多芬的中期作品,依然会感到心潮澎湃乃至热血沸腾的原因。但是,在1812年之后,贝多芬的创作陷入了低潮。随后,其作品风格与表达内涵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贝多芬的晚期风格”从中艰难浮现,最终在1817年至1818年间成型,并保持至去世。贝多芬最后十年的创作,由此成为独立的风格单位,标志着崭新的艺术境界。那么,这是怎样一种境界?在贝多芬中期如此壮观的景象之后,如何还能想象更为卓绝的艺术景观?这正是贝多芬晚期创作所要给出的回答。一个对世界、对人生、对艺术怀有坚定自信并取得全面成功的音乐家,随着暮年来临,重新开启自省之路,通过透彻的再次思索和体察,终于修炼成为一个洞悉世界、并达至涅槃的智慧哲人。
绝对不会,永远不会!贝多芬有opus编号的32首奏鸣曲我都弹过,记得当时还算轻松地弹完op90后,开始自信满满地练op101,然而浏览一遍乐谱后却发现从这里开始作品难度陡然上升,并不是技法有多难,而是从心底感觉无从下手。第一次看op101乐谱的那种震撼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简直是鬼斧神工,这不应该是地球上的产物,而是上帝给人类的赠礼,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去表现这部作品。直到op111第二乐章我才明白,最后五首奏鸣曲是一场宏大的送别舞会,贝多芬在这里送别过去并总结他的一生。op123庄严弥撒给了我启示,这五首曲子都藏着一种深沉、被压抑的欢乐,这些欢乐在op111第二乐章开始溢出,随后以羽化登仙般的一连串颤音送别了钢琴,之后的op123、op125以及晚期的弦乐四重奏则把酝酿已久的欢乐毫无保留地的释放,一切仿佛回到了开始,回到了充满希望的明快的op2。贝多芬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没有炫技、没有浮夸,它们是一种境界的体现,是贝多芬纯粹的艺术追求,是他忘记一切、天人合一的象征。
绝非过誉,作为维也纳乐派的代表人物,承古典主义之上启浪漫主义之下,尤其是他晚期的作品充满着实验性和探索,他32首钢琴奏鸣曲里面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最后的3首,可以说是已经登峰造极了。这些奏鸣曲的写作手段和构思对于前人的超越和对于后人的启发是不能估量的。在手段上贝多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3个乐章结构而是有故意的两个乐章,对于对位的手法使用和故意模糊乐章和段落的界限还有乐章之间的融合衔接之自然,乐思变换速度之快,这些传达自己无拘束之思想情感,都是早起浪漫主义的先兆。还有一点我认为他是在用写作交响乐的思维写作奏鸣曲,所以现在的配器作品也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