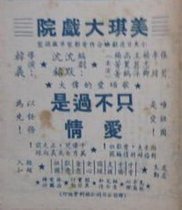我感觉他这人谈不上多高昂,但还是有点理想主义的。杂书馆就是很理想主义的东西,多少爱书人曾经做过的梦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他居然做到了。野心是有的,但是他太清楚分寸和得失了,江湖冰冷,庙堂凶狠,只能这样混着呗。文人骚客如他,要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会不会被资本玩坏了,好在他盔甲够厚,肉够多,伤筋动骨不至于。可惜,文人不是战士,他这种人终究入不了殿堂,受不了朝拜,得不得庙号,只能吃好喝好的长命百岁。安知非福。
每个人对事物的认知度,来源自他最初选择的角度和对深入探索的坚持,这种坚持断然不是高晓松说的”任何事只要坚持就完了“。在我看来,这种坚持更接近他愿意讲这么多年的脱口秀背后所存在的那股子疯劲,准确说就是无关功力与权谋,仅仅是我喜欢,我乐意。而我最初的选择,用我自己总结的一句话叫”我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看到了现实里看不到的真实“。这样一来高晓松的杂文自然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所幸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否则我将永世驻足不前。
高晓松对艺术的理解,包括思想和结构这两方面,很多观点来源于王小波,假如不看王小波的作品,很容易会以为是高晓松自创的。比方说对“有意思”和“有意义”的理解,最早出自王小波的杂文集,王小波主张人要过得有趣、有意思,假如太有意义,就变得没意思。再比如“伟人的胡子“,也是来源于王小波先生对俄国作家的调侃,还有高晓松的国外见闻脱口秀,包括观感、历史和思考三重结构,也能在王小波的杂文《域外杂谈》系列中找到影子。
假如我活到现在,所接触到的文人只有高晓松,想必对他固然会抱着狂信的态度,我是30岁开始读书,客观说我对阅读真正产生兴趣,正是源自高晓松。王小波说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正因为这个观点本身的逻辑成立,我才选择绕到高晓松这个人背后,想看看他后面都站着哪些人,以及从那些人手中出来的作品和观点。
不敢对一个比自己有见识的人评价,但高老师嘴里总会漏出一些炫耀,例如总会说自己的姥姥很厉害,这在《晓说》中大概说了不下五六十次了吧,感觉高老师还是没有真正经过生活的磨难,其实所走的每一步都有后路,人在美好的时刻总会显得从容,侃侃而谈。当然他也说了,他所说的一切只是自己对生活和事物的感受,究竟生活和事物本来每个人对生活的感受都不同。听听聊天还挺好的。
他的出现促进了大众理性思考问题的积极性。换句话说是在帮助全民开智也不为过。他借用自己所处的高位,向我们传递一个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在这里请允许我再次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来证明这种行为的必要性:知识人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