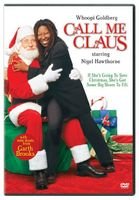王童导演曾任台湾金马奖评委会主席,他作品四度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次数上仅少于六七十年代拿奖拿到手软的李行。王童的代表影片首推台湾近代史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和《无言的山丘》,这个三部曲与侯孝贤的台湾历史三部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加上拍摄时间上相近,堪称影迷观看台湾电影的入门级必修。相较之下,1996年的另一大成之作《红柿子》显得低调无闻,王童仅凭影片获得了1996年金马奖的最佳导演提名。那一年的金马已显疲态,风光尽属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柿子》最终只在最佳美术设计上有所斩获,提名最佳女主角的陶述和导演王童都两手空空,看起来影片并不算成功。然而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的个人十佳里却有《红柿子》的一席之地,它也是选单唯一一部华语作品。虽是一家之见,却也证明《红柿子》有值得挖掘的地方。
对王童的创作生涯来说,两岸往来和解时期,第一时间出现的影片就有《香蕉天堂》,《红柿子》的出现恰好赶逢两岸关系开始恶化,所以影响力被弱化。即便在时间跨度上,《红柿子》与《香蕉天堂》有大部分板块重叠,然而《红柿子》的意义实在非凡,因为这是一次带有自传色彩的阶段性总结。王童谨慎梳理出的成长往事,大部分是关于姥姥和父母一辈人。身为作者本人的王童却被隐没在人堆当中,充当不起眼的观察者之一。父亲王仲廉于1991年入土为安,遗留给王童一个机会甚至是责任去认真、全面地审视父辈。不同于侯孝贤早在80年代就破解了自传的人生难题,王童只有拍完《红柿子》,心口石头方才落地。完成于90年代的《红柿子》散发着熟透的气息,晶莹亮泽、红艳欲滴。此后十年王童都没有恢复到旧有水准,与台湾电影一般江河日下,无处谈复兴。
《红柿子》的内容并非王童百分之一百的个人自传,他吸取身边三个家庭的灵感才创作而成。片中孩子名字的前两个字都是王光,王童本名王中龢(和)。中字变成了光字,正是片中那个爱画画的光和。画肖像画的一段,姥姥还认为光和要考艺术系还需努力,重量级配角刘若英亦在该段出场。王童本人从小对美术绘画感到兴趣,后来也考上了美术系,进入中影公司也是担任美工一职,他在多部影片中的美术指导设计中表现抢眼,后来得以有机会执导影片。
王司令员显然是指王童的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王仲廉。他成为蒋介石兵败退台的牺牲者,带不了兵只能养鸡养牛蛙卖铅笔。无奈流年不利,没一样有见成效。妻子郭翔九曾是大家闺秀,落户台湾后事事操心,租房卖画只为一家的幸福。王家的困苦被父母二人肩扛了下来,生活的落魄程度从他们身上可窥见七八分。《红柿子》的中心人物是姥姥无疑,父亲母亲的位置多少显得尴尬,父亲戎马一生现在却无用武之地,他叫不清儿子的名字,会冲着孩子发火、砸烂自制收音机,看起来是个不受欢迎的角色。母亲忙忙碌碌,更要照顾来台湾后新生的孩子。父母能直观地理解和照顾老人家的感受,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十几口人张开的嘴巴要分去无数精力。
这部电影因接近三小时的片长会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不过《红柿子》讲故事的能力和整体流畅程度是不容置疑。影片的初剪版本是四小时,割舍之后依然稍嫌太长的原因是发自个人的缘故,想要说的东西太多,自然溢满。大陆一段以冷清的黑白画面来营造萧瑟浓郁的时代感,黑白镜头的再次出现是结尾院子里的红柿子树。该段落突出的颜色是红色,挂满枝头的红柿子,无人采摘。王童运用技术突出了红色,之后红色依然是影片有意主打的色调。
姥姥的寿宴酒席、冯副官和奶妈的婚礼、长袍锦旗寿衣,红色的反复出现不是单纯的巧合,它们都与红柿子形成完整对照。一旦由片中人物开口反复提及忆起红柿子就显得矫情刻意,电影只能通过类似表征的红色物体来反映主题,将“红柿子”的意象贯穿环绕,不断承接延续使得《红柿子》显得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