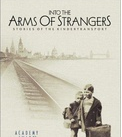村子门口长着一颗老大老大的槐树,到了夏天总有不少老头喜欢往那里凑,图个凉快。老张头也是其中一员。老张头是从城里回来的见过大世面的人,村里的老头老太太都爱找他聊天,聊啥呢?当然是聊城里的新鲜事咯!“诶老张头,你说你在城里过得舒坦回来干啥子哩?”隔壁姜老头随口问了句。老张头得意的笑容僵住了,不过因为满脸皱纹的原因,倒没人注意到。他心虚地掩饰着说:“还能干啥子,城里舒坦是舒坦,这不是没人聊天嘛!”“是没人听你吹牛吧!”众老头笑作一团,但转眼又聊起别的事了,谁也没在意这一句笑谈。但老张头心头坎上却堵着了,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老张头总觉着那姓姜的话中有话,还带着刺!他越想越不是滋味,愤愤地看了一眼姜老头,搬起椅子就要回家。“诶老张头你要去哪?”有人注意到他的动作,便开口问道。“回家!”老张头头也不回地闷声回了句,气呼呼地走了。回到家里的老张头越想越气,他赌气地一屁股坐在了炕头上。“哎呦!”老张头痛呼一声,撅起屁股从炕上掏出了一张相框,他看着相框突然沉默了。相框里面的老妇人面带慈祥温柔的笑脸望着老张头,可惜是张黑白照。老张头看着看着眼眶就有些湿润了,他像个孩子一样把老妇人的照片紧紧地抱在怀里,口中嗫嚅着说“老婆子啊,你咋还不带我走呢!”突然摆置在外屋的座机铃声响了起来。老张头颤巍巍地抬起沟壑纵横的手抹了一把眼睛,放下相框向外屋走去。“喂。”“爸,你怎么不打招呼就回去了?”略带沧桑的男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没咋,”老张头笑了,无所谓道:“住着不习惯就回来了。”“……”电话那头一阵沉默。老张头小心翼翼地问:“咋啦?”是不是阿玲说你了?”男人的声音低沉了几分。“没有没有!没有的事!”老张头慌忙地连连摆手,笑呵呵道:“阿玲那孩子老孝顺了!”男人那边又是一阵沉默。老张头犹豫着说道:“我只是在城里住不习惯……”“爸,对不起。”男人哽咽的声音打断了老张头的话。老张头的手不由自主抖了一下,鼻腔里涌上了一股涩意,他轻轻吸了吸鼻子,笑着说:“没啥对不起的,爸在乡下住得自在,隔壁姜老头还经常来找爸聊天哩!”老张头不等儿子说话,继续道:“行了行了,你忙你的吧!有空……有空回来看看就成!”语罢,再次不等儿子回话就忙不迭地挂了电话。老张头放在电话上的手有些颤抖,他叹了一口气,颤颤巍巍地转身离开,背影已然苍老了许多。
说点纪实的。去老人院看九十多岁的外公,老人们要么在院子里的轮椅上坐着晒太阳,要么就在走廊的排凳上坐着打盹。一个老人耳朵听不到,在他耳朵边喊都听不到。收拾地利索、干净,是个讲究的老头。他从早上开始就手里攥着一把毛爷爷,要往照顾他的男娃(真心面嫩的男护工)手里放:我活不了几天了,我死了,你把这钱给来带我回去的家人。男娃笑:你自己给他们。老头生气,一边摇扇子一边说,“中午别叫我吃饭,我不吃。”据护工说,这个老头代表了一部分老人——我们活的日子不多了。有个老人,脾气倔,当天他儿子也去了,送了块西瓜。问,爸你胡子怎么不刮?老头呛了儿子一句,老板不给我刮。然后拄着拐杖气呼呼地往房间走,抱着西瓜吃起来。儿子在门口与我们聊天,说到父亲这些年换了好多老人院。这个老头也代表了一部分老人——总也见不到儿女。
有一次我在街边的公园看六个老头儿打扑克,看样子最年轻的也得七十多了,最大的得八十多了。旁边发生了一起汽车剐蹭,一台是好车,下来的人是司机说自己做不了主,得请示老板,但暂时联系不上。另一台车下来四个二十出头打扮身材都不错的女孩,估计是刚买新车没多久开出来玩,而且是外地牌照,四个女孩都慌了神的急得的不得了的该怎么处理胡乱打电话之类的,焦急之情溢于言表。这个时候只听其中一个打扑克的老头看了看对其他五个打扑克的老头儿说,要不咱们几个去帮那几个小姑娘把事儿平了让她们陪咱们睡觉吧。另一个老头儿说他相中了白裙子的那个,事儿平完了白裙子的归他,还有一个老头儿说咱们六个人,他们才四个姑娘不够分。一开始说话的老头儿说没事儿,实在不行俩人一个。几个老头说完了淫笑的不要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