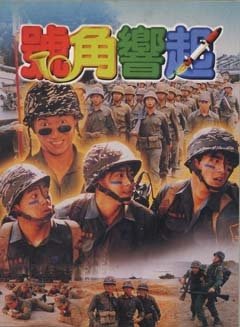柳州话现普遍称为“马蹄”,但是旧时叫做“蒲慈”“蒲荠”,当为“凫茨”的音转,是个老词,今多不用。(见《柳州方言词典》),马蹄是较为晚近传入的粤方言借词。问题是deih为旱地,而荸荠只会生长于naz(水田)中,为何不称maknaz?另外部分壮语中maxdaez前再可冠以通名mak,显然maxdaez更有可能是个凝固的词组,max并非通名mak的弱化。并且此称呼的区域和粤语区过于重合,谁借谁都还不一定呢。所以马蹄为壮语“地下果”的说法可能有点武断了。
biqi(第一个字二声,第二个字轻声,音似“鼻涕”)天津叫法跟大多数地方都一样,没什么特殊的。当年姥姥问我吃不吃荸荠。我说你太恶心了,不吃!她就坐在沙发上,就着垃圾桶,拿菜刀一点一点削荸荠。我蹲在跟前看她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荸荠这东西小,而且扁圆,不太好削。明明外皮是黑紫色的,里边的果肉竟然白嫩可爱。姥姥也不着急,就磨磨蹭蹭的,看得人心急。好不容易削完一个,我正要伸手。她往嘴里一送。“嗯,还挺甜。”
家在北方,日常就读作荸荠;现在在南方上学,身边同学大多读成马蹄;(每吃一只荸荠,就有一匹马失去它的蹄子。之前我还专门跑去问重庆的妹子,她说“慈瓜儿”,我听成刺根儿,看见之前的一些回答才明白过来;上海人还有比较特别的叫法,“地栗”或者“地梨”,“栗”是因为荸荠的外形和功效跟栗子相似,“梨”么,大概是由于荸荠清甜多汁吧。
襄阳话叫“不计”从我记事起,每年过节家里都会买上几斤当年货,当然了,大年三十吃团圆饭的时候,必上的一道菜就是荸荠,大人们会告诉我说,吃了这个东西,不管是过节还是平时,说话的时候就会说比较吉利的话,不会胡说八道。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过年餐桌上还是少不了这个,以后等我有了孩子,我也还会让他吃这个,好好做人,好好说话。
噗(pu)舅(jiu)。安徽话,有什么由来来真的不清楚。话说还是小时候经常吃的。有人用小扁担挑着两个小筐子。沿街叫卖,几块一斤。奶奶时常买个几块钱的,用一个塑料袋拎回家。每次在路上我都想伸手偷吃几个。奶奶很快的打我的手,说,没洗,不能吃。因为我一般都是直接拿着,用牙啃去上面的头,然后就是咬去皮,直接吃。
马蹄在潮汕地区称为钱葱,原因是它的叶子跟葱很相似,从正上方向下看,像个圆的铜钱,所以有“钱葱”一词。我们这边拿来生吃,做汤,也可以拿来煮成“青草水”我听家里老人说用这个泡水喝,可以治疗感冒。我姥姥就经常喝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