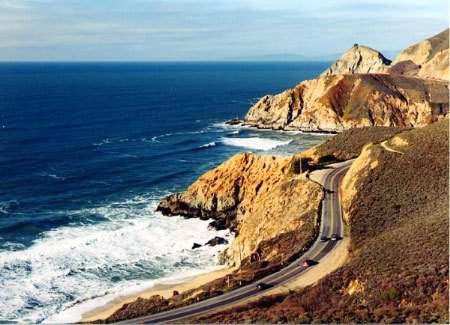我主要从作品风格上来分析吧,这样比较客观。
1.从人物塑造上看,安妮宝贝选取的都是社会的边缘人物,他们在某个区域倍受压迫,也在某个场景过度放纵。
都市边缘人背离大众生活轨 道, 无法实现人际间的温情交往, 他们多以单独个 体的行式行走在都市人生的边缘, 不被周围人群 理解接纳, 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同事的温情关怀, 对都市营营役役生活下的孤独、冷漠有一种脆弱 敏感的接收能力, 他们变得自闭, 孤僻, 不相信周 围人群和人间温情, 封锁自己的心灵、埋葬自己的 美好追求, 产生一种严重的信仰危机。
2.从句式上看,安妮宝贝很明显的简洁风格。语句弹性,跳跃,大量使用句号。
安妮宝贝的小说多用单句、短句, 包括独词句, 非主谓句。很少使用复句、长句, 这使得她的小说语言显得格外简洁、空灵、直指人心。短句的写作方式在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是最常见的。
3.从修辞上看,她大量使用比喻,白描等手法,是文字变得轻柔,感人。在本体和喻体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点,这种内心无法诉说的情感一旦被委婉揭示,就会有所触动。
4.在安的小说中,容易看见意识流的影子这正是杜拉斯所擅长的。毫无疑问,安的小说比杜拉斯的易读,但是在杜拉斯言语的丰厚程度面前,安的显得略有伤春悲秋的无病呻吟,她表现出来难过,但这只是人性的一部分。当然,在手法上,安确实也有过人之处。
更多的文学解读,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我从心理学和文学的角度,为你破解生活密码。
微信公众号:文学有毒
有趣轻松的文学解读,别轻易关注,小心中毒。
最初知道安妮宝贝是在高二,她还没有名气,《彼岸花》刚刚开始在《萌芽》上连载,阿文最先读过,开心的拿给我说,你看,写的真好。那些字就躺在那一摞厚厚的打印纸上。差不多相同的时期,还有郭敬明的《幻城》,以及因为新概念作文而走红的一撮人。就这样用复印稿看完了几部小说。在安妮宝贝的阴影里,成长。
尽管现在我再也读不进安妮宝贝的任何文字,她的新书我还是会习惯性的买回来,小心翼翼地全部保存好,像一个纪念仪式。我们,这样过了读安妮宝贝的年纪。
曾经和朋友开玩笑地说,如果有一天遇到安妮,我很想问她,你为何背叛了那些因为你而等待一个穿着白衬衫球鞋眼神明亮的男孩的女孩们,而嫁给了一个富商。这让我们,有点痛恨自己无知的青春。
《七月与安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还专门买了一本漫画版。这部话剧的排演,让回忆蠢蠢欲动,那些日子呼啸而至。坐在靠窗边的位置上听着歌发呆的我,静静的传来传去的小纸条,走廊尽头那个穿着黑色衣服抽烟男孩的背影,改名字叫做七月的女孩,说要去流浪然后在最喜欢的地方为我种一棵树的人……《七月与安生》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站在这个年纪里,可以光明正大的再矫情一回。
几年以前,有位文学圈儿内的朋友跟我说:“安妮宝贝的小说是从网上发迹的,她是网上出名的写手,如今却远离了网络。” 起先,我还不太相信这样的说法,但一直到了今年问过安妮宝贝本人才知道她如今不那么热衷上网。不过,至于无“我”的行文是从何时开始的?这个没问得过多,因为两年前她在北京就告诉了我,不多用“我”的行文完全是有意识的。从网络里走出来的女作家,想必这也是外国关注中国文学的一个热点,至少日本如此。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量介绍当中,安妮宝贝的存在跟她绮丽的行文一样,也许是一个另类。下图是日本共同通信社这个月发表的采访记。日本的文学评论认为她的小说具有跨越国境的重要因素,同时她也表示会按照这样一条思路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