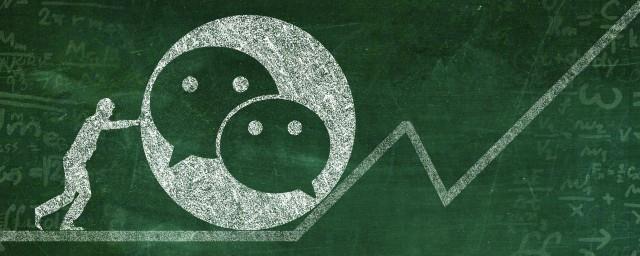鲁迅先生对郭沫若的意见,始于郭沫若等人对鲁迅的攻击,他们认为鲁迅先生“不够革命”,尤其是创造社成仿吾、冯乃超等人,认为鲁迅先生没落了,代表的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不代表无产阶级。鲁迅因此对创造社这帮人很有意见,这意见也不是针对郭沫若一人,而是针对创造社,他撰文指出创造社文学理论的错误,创造社后来对鲁迅的攻击则掺杂了许多人身攻击,郭沫若身在创造社,自然是无可避免地参加了论战的。到了后来,鲁迅在“两个口号”的论战中,表明他对郭沫若的见解是认同的,郭沫若得知鲁迅的态度之后,非常感动,立刻反省自己,他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鲁迅“彻底钦佩”。还检讨了自己不应该没有见过鲁迅就去骂鲁迅的行为。不久之后,鲁迅先生去世,郭沫若闻此噩耗,连夜写了一篇悼文,紧接着又写了一篇《坠落了一个巨星》,给予鲁迅非常高的评价,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很多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
胡适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便是新文学运动的干将,两人曾交情很好,互相赞美,但是在五四运动结束之后,两人开始有了小缝隙。鲁迅之骂胡适,一是因为1922年胡适去见溥仪的时候,称呼溥仪为“皇上”。在1932年,宋庆龄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本来也是这个同盟的北平分会主席,结果他不但不支持同盟,还认为上海分会转给他的两封关于监狱打人的检举信是捏造的。他的言论,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宋庆龄和蔡元培要求他更正,他也不予理睬。到后来,同盟的杨杏佛被特务在上海暗杀,胡适居然不发一词。而这位杨杏佛,曾是胡适的学生和朋友,胡适性格中无情的一面,展露无疑了。
梁实秋是鲁迅的主要论敌,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是批判梁实秋的。梁实秋与鲁迅两人的根本分歧在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从中也可看出两人世界观、价值观的根本不同。近百年过去,我们不再评论两位老先生孰是孰非,但毋庸讳言,经过这次论战后,梁实秋成为左翼作家攻击的靶子,以至于1949年后在大陆遭到几十年的口诛笔伐。其实凭良心而论,梁实秋是一位善良、宽容、博学的学者,他的文字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非常耐读,其中尤以《雅舍小品》为妙。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在重庆北碚梁实秋故居雅舍所拍。
徐志摩与鲁迅先生的龃龉,始于鲁迅先生对徐志摩的诗风不喜,不过那时还没有到人身攻击的地步。但是后来在鲁迅和陈西滢的斗争中,徐志摩和陈西滢在《晨报副刊》弄了个“攻周专刊”,把鲁迅骂了一顿,后来李四光也参与进来骂鲁迅,在鲁迅还没有来得及还击的时候,徐志摩就拉偏架,让双方“带住”,鲁迅又没有骂人,怎么就叫人家带住呢?何况徐志摩本人也是攻击者,居然还能装作和事老,鲁迅自然不会就这样“带住”,第二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还击这三个人,文章名曰《我还不能带住》。
杨荫榆并非有人认为的柔弱女子,与此相反,她在开除六名学生之后,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暴烈学生之感言》,以婆婆自居,把学生比作一群童养媳,激起鲁迅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与其他六位教授,发表《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坚决支持学生。与之相对,陈西滢将女师大比作“臭茅厕”,鲁迅则飞快地予以反击,陈西滢又说鲁迅与同籍文人拉帮结派,鲁迅还击说陈西滢也和杨荫榆同籍——如此种种,陈西滢挑事又骂不过,最后写信给徐志摩哭诉。
梁实秋和鲁迅之间因为“文学是否有阶级性”争论过。梁实秋说鲁迅是资本主义的走后,说自己就算是资本主义的走狗也不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谁,不像那谁谁谁腆着脸去领卢布。鲁迅怼人确实有一套,顺着梁实秋的话就说“有些走狗,因为是资本家养过的,但是没有家,饿的精瘦,成了没人要的野狗,依旧习惯见了穷人就吠,见了资本家就摇尾巴”。从此梁实秋就被扣上了“资本家的走狗”这么一顶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