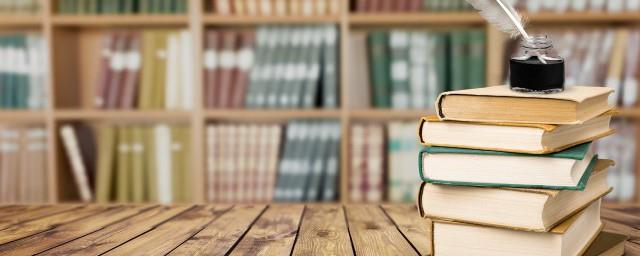《甄嬛传》重构了一个男性处于绝对主宰地位的世界,强化以女性的绝对服从为特征的内在秩序,剧中两性关系的实质是占有者(皇帝)与被使用物(嫔妃)。在这种以“主宰--服从”为特征的秩序中,电视剧反复强调女性(嫔妃)取悦于男性(皇帝)的必需性与正义性,为两性的不对等关系做了大量日常化、正常化的铺陈。嫔妃们不仅要为悦己者“容”,甚至应当为悦己者“生”,嫔妃完全按照皇帝的喜好与理想开发和展现各种技能与才华。女性的真实自我被遮蔽了,女性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并以悦己的目的生存。对嫔妃而言,任何才情如果不受外在评价的承认,就不配称作才情。
女性变成了客体,以可能“被发现、被使用”的物的拟态形式去完成自我塑造,嫔妃们的“奋斗史”也就是女性将自我彻底“他者化”、“客体化”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将《甄嬛传》比为宫廷版的《杜拉拉升职记》完全不合适,因为后者中女性的自尊与觉悟、独立与自强远不是伪女性视角的《甄嬛传》所能企及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父权社会“建构”而成的。这种“建构”依赖传统社会的两性观念,作为社会观念载体的文艺作品,其中被反复强化的典型女性形象,正是由男性按照自我理想塑造的女性模型。《甄嬛传》大量铺排外表美貌、(对男性)行为顺服的物化形态的女性典范形象,其间表现的所谓女性内心和女性之间的世界,不过是一种站在“伪女性”立场上对男性逻辑与父权框架的重申。争风吃醋的嫔妃们不过是一群被囚于皇宫里、对主人百依百顺、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性奴。正因为如此,毫无性别自觉与反抗意识的嫔妃们,她们遭受的痛苦不具有悲剧感染力,她们的个别成功也不具有喜剧效力,她们相互间的倾轧与阴谋斗争更不具有革命性、现代性或积极现实意义。
《甄嬛传》塑造了一群人人相害、人人自危、行为极其丑陋的嫔妃、宫女、太监,但几乎没成功塑造出一位令人欣赏的“人”。剧中人几乎每一个的手上都沾染过鲜血。试看宫廷中这些人做过的事:直接的暗杀就有好几回(如推人溺水),各式各样的香料投毒被众人所倚重(上至帝、后,下至妃、嫔、贵人、常在、宫女都很常用),有的巧妙地借刀杀人,也有的自施苦肉计,还有不计其数的打小报告、诬蔑、造谣生事(许多这类言语导致了死亡事件),甚至有散布传染病这种危及公共安全的举动,而利用巫术整人这类无实际效用的小儿科计谋则遭到了无情的耻笑。
嫔妃当中,就算没有过实际行动害人的,也都善妒、心胸狭窄,都用“风刀霜剑”似的冷言冷语无情地伤害过同性,甄嬛本人就用“人彘”的故事恐吓一名贵人并令她变成了疯子。“人”在《甄嬛传》中是缺席的,花枝招展、锦衣玉食的嫔妃们却像一群相互撕杀的嗜血野兽,人的高贵、人身为万物灵长的卓尔不群被无限贬低。
《甄嬛传》中异化的不仅有爱情,还有亲情。皇帝因为一嫔妃的“美色”不足,连带不爱这名嫔妃所生之子,居然几年不见亲生儿子一面,令无辜的小阿哥倍尝人间冷暖。皇帝为政治利益嫁妹于年迈的准格尔汗,令亲妹妹痛不欲生。甄嬛的亲妹妹也因为嫉妒姐姐的美貌与幸运,竟然替甄嬛的“劲敌”华妃充当“内鬼”。
剧中亲子关系、兄弟关系、姊妹关系,无不竞相扭曲,人间真挚的亲情被一一抹杀。剧中所有嫔妃均以“姊妹”相称,但她们之间的实际关系却势同水火,看似要好的嫔妃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盟友。盟友当然是以利益为首要考量,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是也。考察甄嬛真正的朋友,只有两名:老早对皇帝冷了心的眉庄与年幼即遭非命的淳儿。眉庄一心侍奉太后,这就意味着有靠山,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益的权力资源;淳儿尚未成年,对甄嬛言听计从,易被拉拢和指使充当前锋。不构成竞争、有利用价值,这就是甄嬛所能给予友谊对象的条件。眉庄、淳儿之于甄嬛,正如安陵容之于皇后、曹贵人之于华妃等,剧中的友伴们无不是借友情之名,依各方势力与利用价值为根据形成的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