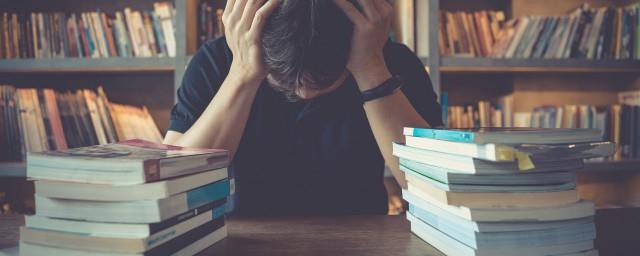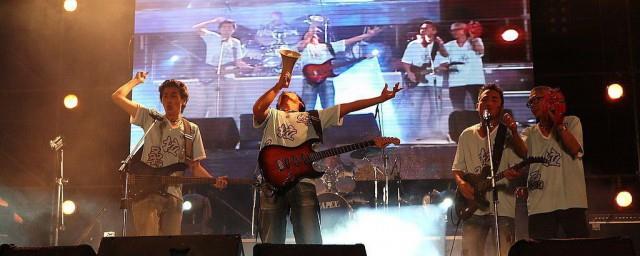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有个性脾气的,这是一种天性。内向的人,多数时候把脾气发在内心里,一旦对外发泄就异常凶猛;外向的人,随时随地可能发脾气,有点小任性;混合性的人,有时把脾气装在心里,有时把脾气发在外面。人是有灵性的高级动物,特别是通过受教,深知脾气的负面有害性。所以,虽然有脾气,多数人一般情况能约束自己。即使发脾气也比较讲求和注意事因、对象、场合、时机。一部分自律性强修养高的人,抑制能力和转化情绪的能力非常强,往往表现的没脾气。而极少数的人,缺教养少自律,心态不正,点火就着,经常乱发脾气,很令人生厌。
过去我们有对团体的忠诚和归属感,但现代社会已经走入了陌生化生存的阶段。人们无法找到借以慰藉的稳定力量,以至于妨碍了情感的“确认”。就像小时候一样,只有对坏妈妈的分离确认,而没有找到对好妈妈的认同感。处在这样疏离的社会中,人们习惯于自我为中心,不觉得在世界上拥有稳固的一席之地。当社会关系不能给人提供稳定的安慰力量,个人为了要建立操控感与熟悉感,便可能产生各式各样的不当行为,像自我认同感低落、人际关系恶化、孤独、寂寞、无聊的情绪、以及冲动行为、无名之火,这中间的失控与沮丧只能作用于自己或最亲密的家人。
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大家的角色都比较单一。今天,自我实现的途径多元化,人们对男性的要求是也要参与家庭生活,要展现丰富温柔的情感;对女性是也要建立职场角色,展现强势的一面。人们在自我认同和角色定位上开始有了各种需要平衡的东西。在各种选择中,人们的内在焦虑会变得很高。而整个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以及信仰系统缺失,让人们的内在常常处于深深的焦虑和不信任当中。
我们整个社会对秩序有一种追求。科学追求精密,文明追求进步,我们的世界拥有各种好与坏的是非标准,然而,一个健全的社会,可以接纳多元化的事物。如果试图消除多元化,无视不确定性的存在,只会增加我们的焦虑。当一个人处于这种社会的压力中,会对自身的各种不稳定性因素心存恐惧,也成为压力的来源,这种说不出来的压力,只能周期性找出口爆发给最爱的人。
“窝里横”人格,都是在外是条虫,在家是条龙。他们缺乏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能力,只有在安全的关系里,才敢于展示真实的自我。对他们本来应该去爱的人,反而采取了“暴力”的伤害。他们的潜台词是“如果我对你发脾气,你都没有放弃我,那么我就是被爱的。”在这样一类人身上,很可能缺少一种能力,即用爱的方式而非伤害的方式来建立关系的能力。
如果一个人能够对爱的人表达“我需要爱”,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需要爱的人,是把自己放在弱势的位置,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主动把自己放在弱势的位置呢?恰恰是具有强大内心的人。而一个人用愤怒的方式表达亲密,很重要的原因是愤怒是一种“有力量”的假象,他要用它来应对自己的“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