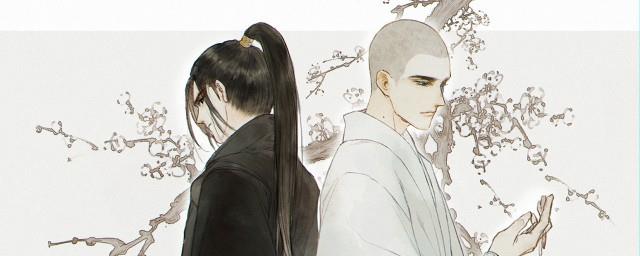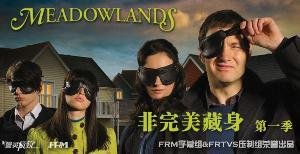如果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那么别人的赞美攻讦议论又怎么会去在意呢?诚如叔本华所言,一旦我们充分了解了他人思想的肤浅和空洞的本质,他人观点的狭隘,他人情感的琐碎无聊,他人想法的荒谬乖张,以及他人错误的防不胜防,我们就会逐渐对他人大脑中进行的活动变得漠不关心,我们就会明白任何一个过度重视他人观点的人给了他人过高的尊严。过多地关注那些在我们的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的看法,是我们把自己短暂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只有那些击中目标的谴责才能使我们收到伤害,我们个人的品质不应该取决于他人的评价,难道和氏璧没有得到楚王的认可,它本身的价值就降低了吗?难道李白被放逐夜郎,他的诗文就不震铄古今了吗?当我们真正认识了自己,也就不会在乎一大群路人甲乙丙丁形成的随机群体对我们的看法了。另外值得提的一点,不要无缘无故接受别人的批评攻讦之词,也不要无缘无故接受他人的赞美,显然,后者更难。无论什么样的评价,先经过理性分析,到底是不是说中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是而已。
过度在意别人评价,反映了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强大的张力。一般来说,幼时很少得到肯定与赞赏的孩子,或者经常被批评与贬低的孩子(比如那个女孩),容易出现苛刻的理想自我。因为当现实自我无法被肯定时,便只能通过理想自我来实现它,这相当于自恋需要的延迟满足。相反,一个幼时经常得到适度肯定的孩子,则会形成有弹性的自我理想,这些人能更多的欣赏和认同现实自我。成长过程中理想化父母(每个孩子都渴望自己的父母是优秀的)的缺失也会导致理想自我的苛刻。当一个人的父母是没有地位的、无法自控的、懒惰的,被人瞧不起的形象时,难免会使他的理想化双亲需要受到创伤,从而执着于原始的理想化状态,无法转化为健康的自我理想。
你对自己满意吗?很少有人能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些牛皮吹得很大的人,或者沾沾自喜于一些成绩的人,看上去很自信,但其实对自己很不满意,不满意到只能靠幻想中的成功来安抚自己。文化以制造对自己的不满意为己任,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知足常乐并不是被提倡的态度。从阶级关系来看,当民众们对自己很满意时,谁来替统治者卖命地干活?看来,通过塑造成功形象,制造等级差异,普遍营造“你还不够好”的信念,是统治者对个体的御心术。吊诡的是,社会又要求个体能“自尊、自爱、自信”,社会意识与社会潜意识的分裂可见一斑。
越来越觉得别人的看法真的没这么重要。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如果一开始就想让每个人都满意,那到最后就会变成每个人都不满意。有些行为,看似中庸,实属平庸。与其如此,不如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说好自己该说的话,至于那些闲杂人等,实在没工夫顾及他们的感受了。喜欢你的人,什么都不用做依旧喜欢;讨厌你的人,做再多还是讨厌。既然如此,何必自寻烦恼。自己的人生,与别人无关。
。有的人你第一眼看到就很喜欢,哪怕他什么都没做;有的人刚见面就觉得不顺眼,总觉得哪里让自己不舒服。这就是人的喜好,或者说偏好,无法改变。也许是因为长相、也许是因为气质、也许是因为一些细节,总之,这种纯粹主观意识的判断很难通过客观的行为来改变。既然如此,就随他去吧,何必辛辛苦苦让那些本来就不喜欢自己的人改变看法,他们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经常让自己处于“存在”状态,这可谓是最彻底的摆脱评价的途径。存在是去体验,去创造,去给予;是去接受新鲜的思想和变化,好好地活在当下。习惯于评价的人,很难有存在的状态;而保持在存在状态下的禅修者,则较少有评价性态度。禅修是对治自我批评的良药,长年禅修的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也保持觉察的习惯,充分的抑制导致抑郁情绪的自我批评。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读读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