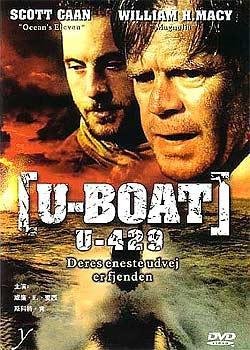那时候农村生活很枯燥,小孩子只能走雪橇。二根细木,每根直径约五公分,太粗不轻巧,细木硬度得好一点,否则容易折断。长短一般六十至一百二十公分,根据身高而定。在离地三十至五十公分的细木棍上打个方孔,装上脚踏板,再细木棍的一端按上十公分长的横木扶手。一付简简单单的雪踏橇完成。整个冬天一遇下雨或下雪天出门的必备的脚上工具,虽然简陋,但是那时候真的很开心。
那时农村小孩没雨鞋,只有布鞋,都是做妈的晚上熬夜赶制的。一针一针,密密麻麻用粗线穿布鞋底的,再加上用余布自制的布圈。整个冬天晚上做妈的缝制鞋化去很多夜。妈的辛苦鞋,哪里随便踏在湿泥里、雪地上,踏橇正好派大用场。农村孩子个个会走雪踏橇。踩在雪里,一个个圆溜溜木棍印,也是一道风景。一群小孩在一起,难免起哄,踏雪橇碰人。看看谁碰倒的人多,谁的本事大。难免有时人倒橇毁,大哭一场,才肯罢休,现在想想那时候很幸福。
冬天的早上特别冷,不上课。我每天就起的特别早,然后拿着书在胡同口背古诗。有时候也会偷偷地跑到学校,在黑板上把当天考试的内容默默抄写一遍。那时候,我是一个那么爱学习的孩子。遗憾的是,我那么努力,最终还是差一点没考上大学。因为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从学校里逃了回来。以致于现在我都对当年的决策耿耿于怀。
冷,真冷。冷的每天看到太阳都不想走,躺在被窝里都不想出来。那时候家家屋檐下都是琉璃柱。池塘里结的都是冰。大人们凿冰捉鱼。小孩捡冰用笔芯在冰上吹小洞,然后串根线抬着走。还有一次,我在池塘里滑冰,冰破了,鞋子裤子全湿了,回家挨了一顿打。
现在想起来,儿时真是想尽办法,疯着的玩。那时候,总觉得比现在要冷得多。冬天的水沟,池塘里总是结满了厚厚的冰。那时候的我们,拿瓦片冰块上飙,看谁飙的快,看谁飙的远。有时专找冰厚的地方,慢慢的试探着走,虽然前俯后仰,引得却是开心的大笑。然而,儿时农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吹冰窟窿眼,串起来玩。那时,我们砸出一块厚厚的冰,放在稍高点的砖块上,找根短空心瘦竹管,对准冰块边缘的一个点,鼓起腮帮,使劲的用力吹。冰在吹的暖气下,慢慢的融化,先是浅窝窝,慢慢的深了些,最后一个冰洞渐渐的形成。看着洞眼深了,心里那个像吃了蜜的甜,撅起屁股,吹的是越吹越有劲。看看这边的洞吹出了大半深,再换上另外一边,对着洞的方向又加劲的吹。那时候倒不觉得冷,倒是吹出了汗,吹的脸满是通红,吹出的满满的暖意。
农村的冬天记忆深刻,工厂之外就是田野和山坡,再远就是叠叠青山。记得寒冬腊月去上学,手里拿着白馒头,有的里面夹上白糖,有的里面夹上梅干菜,挎着绿书包,蹬着妈妈纳的棉鞋,穿着棉袄,和小伙伴一路走一路玩去学校。冬季,霜降普遍,公路边的草上都蒙了层白蒙蒙的霜,田野里的一陇陇麦地也都蒙了白,阳光下晶荧闪光,煞是好看。再冷,结冰是常有的事,屋檐下挂着条条冰锥子,路边有水的地方都结上了冰,常穿着鞋去踩结了冰水洼,池塘边拿块石头砸冰。儿时的冬季乐趣总是很多,那时天总是很蓝,还不知什么是污染,天气比比现在冷,结冰是常有的事。更重要的事,天气冷了,离过年的日子一天天近了。一到过年,有新衣服新鞋,还有红包,还可以贪婪地深迷于连环画,家家户户年底杀猪宰羊,鸡鸭鱼肉平时吃不上的这时候都能解馋了,呼亲换友,左领石舍,今天王家明天李家串户过年。那时候也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家里做的,切糖糕、蒸发糕、炸番薯片、炒花生瓜子、写对联、贴福字、放鞭炮,那年过的才叫红红火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