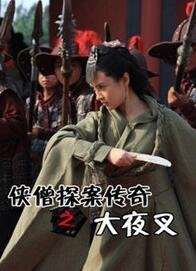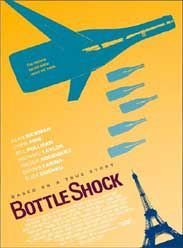话说回来,我们看一个故事,往往是上帝视角,以俯视的角度去打量。故事是一个完整的三维空间的故事,但我们在那个三维世界之外,就像上帝一样俯视着剧中人物的一切,拥有一种第四维的视角。而乔治·马丁大神在《权力的游戏》则创造了一个POV的视角,以剧中某一角色的眼光去讲故事,这一角色的视线只能看到感受到自己所见的部分,ta看不到的地方,就全无所知。观众跟着POV的眼光去打量剧情,就像剧中的一分子,置身于三维故事世界之内,不再是上帝,需要更多动用自己的思考去揣摩故事的走向,人物性格的变化等剧情。《罗曼蒂克消亡史》中,陆先生(杜月笙)的就是整个故事的pov视角,故事大量留白,给观众以极大的想象空间,以填补导演未说尽的故事及意蕴。这没什么错,用好了,非常考验导演的执导能力。较为传神的地方在于,导演程耳将上帝视角交给了一只猫,只有它可以窥见一个巨大阴谋的全部。
就故事而言,《罗曼蒂克消亡史》在开篇之初有一个规模宏大的架构,有纷扰众多的人物线索。隐然有一种《美国往事》的气势。故事聚焦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那里有陆先生一家,围绕着他,陆续展现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人物图谱:叱咤风云的帮派大佬,不甘寂寞的交际花,说着地道上海话的日本妹夫,只收交通费的杀手,被冷落却忠诚的姨太太,外表光鲜的电影皇后,深宅大院里深不可测的管家,偶尔偷腥的电影皇帝,荷尔蒙满溢大脑的帮派小弟,一心想要破处的处男,善良的妓女,随波逐流的明星丈夫,投靠日本人的帮派二哥,日理万机却抽空恋爱的戴先生。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一个群体,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充满了浪漫与激情气息的旧上海。
浪漫,英文说法是romantic,音译过来就是罗曼蒂克。《罗曼蒂克消亡史》,说的就是曾经繁华激情浪漫的旧上海逐渐消亡的过程,这个片名就足够看出导演拍摄一部史诗剧的野心。而见证这一个消亡的证人,就是陆先生。曾经,他近乎拥有整个上海,到最后却落得只身一人流亡香港。这个过程,就是另外一个《活着》里的富贵,只身书写的形式不同,具体的展现过程也不同罢了。
不过,《罗曼蒂克消亡史》从2014年就居于华谊当年片单上的影片,结果断断续续传来一些消息,三年都快过去了才终于在2016年的年底上了映,拖的实在是太久了,如果程耳能够更自由更从容一些,最终的呈现应该会好一点吧。但即便如此,依然可以看出导演不一般的掌控能力,隐现出超强的执导能力。
上面说到《罗曼蒂克消亡史》是一部《活着》一样的史诗,其实没有错。《活着》以富贵这样一个普通人的眼光,讲述数十年的时代变迁;《罗曼蒂克消亡史》同样是以一个人的眼光来讲述十余年之间上海滩的风云变幻。恰好的是,这两个人还是同一名演员。不过,葛优葛大爷近些年接严肃片时比较谨慎,更多以喜剧形象现身,以至于有些定型,看他严肃地讲台词,常常会出戏。但实际上葛大爷的戛纳影帝货真价实,没有半点水分。
尽管没有明说,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罗曼蒂克消亡史》讲的是上海滩大佬杜月笙的故事。杜月笙在历史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性格也极为丰富,他的身上有许多故事可以挖掘,不过程耳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并没有去充分挖掘杜月笙丰富多变的性格特点,而是以他为支点,来直视时代的变迁。程耳的选择,有些失策,等于没用好葛优,没有充分发掘他的演技。葛优的表演有些程序化,喜怒不形于色,仅在微妙之间传达情绪,这对演技的要求极高,但对于观众来说却还是更偏爱稍有些夸张的表演,因为那样更具感染能力。就欣赏性而言,程耳与葛优在此都不足以满分。
窃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峰是余华,而不是莫言。余华成就最高者为《许三观卖血记》,其次是《活着》。但《活着》由于在1994年被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并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大奖,顺便为主演葛优带来了一个戛纳影帝的头衔,因此这部作品更为人所知。
《活着》当然是佳作,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很优秀。它通过主人公富贵的视角,将民国至文革数十年的时代沧桑,凝于一身之上,展现出无尽的苍凉与慨叹,是典型史诗级的作品。
电影《活着》出炉之后,眨眼就过去了12年,正好一个轮回,曾经的搭档张艺谋与葛优再次在同一个档期里相遇,只是不再是同一部影片,繁华不再。张艺谋执导的《长城》与葛优主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同一天上映,《长城》的野心比当初《活着》时更大,但没有了余华一流的原著做支撑,只剩下了一个浮华的外壳,内容的空虚招来观众的种种不满,让张艺谋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葛优主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也没有《活着》那样惊艳,葛优的表演也缺乏富贵那样的层次感,显得有些僵硬。但是综合比较的话,《罗曼蒂克消亡史》足以甩开《长城》十二条街。更让人感慨的是,我们有幸见证了一个曾经伟大的导演的堕落,同时见证了另外一名伟大导演的冉冉升起。程耳,经过《边境风云》的暂试新声之后,在《罗曼蒂克消亡史》展现出了他不俗的掌控力。作品当然不完美,甚至存在巨大的缺陷,但程耳已足够证明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