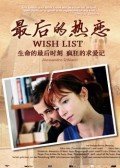《浮城大亨》是严浩导演的最新电影,郭富城主演。关于严浩和郭富城,后者自然不必介绍,而前者,知道便是知道,不知的说也白说。我总觉得,优秀的电影不能用一二三四的技术手段来进行影评,因为那些算盘匠的活计不适合对优秀电影进行感情共振。看《浮城大亨》像在读一部有生命的小说,进去之后,一品味道,又像张爱玲的浓而不黏。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认认真真看完之后,竟然发现里边有很多跟我共振的东西,换言之,这些电影符号伤了我。
郭富城饰演的布华泉,少年时代,在香港的渔船上长大,贫穷一直是伴随他长大的生活状态。父母打渔,养活几个孩子。后来父亲死在海里,母亲没办法,把孩子们送进耶稣学校和别人家里。这些生活经历,在富足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是没有体验的。影片的主角布华泉,作为长子,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因为贫穷导致的“失散”而无能为力,虽然已经处于壮年。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说过,我是种地的出身,这些贫穷的经历都曾撞上过。当你处于壮年而依旧无法改变一些因为贫穷等原因导致的悲惨境地的时候,便知道了《浮城大亨》里边布华泉的大无奈。
跻身上流
贫穷出身的人,要改变贫穷的境地,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便是跻身上流。布华泉通过东印度公司逐渐走到了英国的上流世界,虽然英伦贵族从未接纳这个人,但香港以前的船老大却认为布华泉便是上流了。这也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的男人的尴尬。为了跻身上流,我们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比如,独立人格等等,国语里边有一个比较褒义的词定义这个感觉——忍辱负重。其实,每一个外人看着业已成功的男人,都会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不外乎,儒雅的装孙子。布华泉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是这样。
一个帮你跻身的女人
出于贫穷而能实现跻身的男人,提携你的除了伯乐,其实都少不了已经在上流的女人。这个女人肯定不是你的初恋,甚至于不是你的第一任妻子。为了实现跻身上流,你不得不放弃初恋,或者妻子。我所认识的一些所谓的上流的男人们,貌似都是这样的,可拍的事实。你不得不承认,在一个等级森严的时代里边,只依靠自身的才华是根本不行的,必须要有已经上流的女人帮你,而且帮你的条件便是,你必须要付出自己的身体,及至感情。男人的向上爬,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女人存在是不是不道德的,但我却知道,这也是一种男人面对生活的妥协。到影片布华泉慢慢地推开这么个女人之后,我们仿佛看到了更多的男人不为人知的苦楚。
尽管香港电影新浪潮早在多年前就已完结,昔日的干将只剩徐克、许鞍华依然在主流影坛游走于徘徊,大多新浪潮导演已很难有做为,在商业电影趋之若鹜的今天,“新浪潮”一词仿佛如同传说一般被供奉与祭奠在香港影史之中,偶然想起,都是佳话和谈资一枚,虽然那段历史和往事无法被再度复刻,正如当年的忧伤和愤怒俨然已被毫无风尘的质朴所取代。
2006年的谭家明不再是剑走偏锋的年轻人,他收敛了锐气以更为成熟理智的态度拍摄了《父子》,这时或许人们应该感觉到——后新浪潮的尾声和余味,已是不再忸怩做作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更理性的尊严,许鞍华则用《天水围二部曲》呼应了谭家明的行动,仿佛宣告了新浪潮应有的时代呼声——纵使掀起了香港电影文艺复兴的热潮也代表了与当今市场全然不同的立场与态度,哪怕这股热浪,早已与新浪潮的初衷截然不同。
在新浪潮导演之中,属严浩最为“故我”,哪怕横跨几十个年头,其文艺气息始终不改,从新浪潮开始到结束,再进入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有好的题材才敢拍”注定了他始终是一个落寞的才子,心思细腻的他每每会赋予电影中的主角更多的内心展现来传达导演本人对于事物的态度和感受,从这点上来说,《浮城》就很好的完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完整对应。
或许曾经新浪潮时期电影中的“新”在现在对于观众来说已很陈旧,但严浩并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浮城》中,画面构图,色调以及飘摇的镜头依然非常考究,带有象征意义的镜头不需多加修饰一笔带过,而需勾勒出时代背景的地方也不惜费几尺胶片而全景展现,有舍有得,几帧美景画面只是调了调色而已,但表达的质感与CG场景炮制的效果还是截然不同,这样老式的做法非常考验导演的真章,足以让人惊呼香港电影久违了的对于映像细节的追求。
片头何超仪饰演的布母在被风浪吹打的船只上流产一段,周遭全黑,灯光仅打在人物和道具上,而周围的黑暗则象征了人物仿佛无力选择命运的无助感,从开头一段至少就用了非常风格化的图像点明了“浮城”之外犹如困笼或巨浪一般形成了让人无法喘息的城墙,然而无论是城市还是渔船取景,严浩都着重表现了墙体对人的限制,电影中鲜少有开阔之景。
然而墙体的设定对于严浩来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一个层面,象征的是人情淡漠的隔阂,严浩对于60年代香港人情的势利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在求表叔借钱一段,背后是压抑的灰黑色土砖墙,
然而最后释然一场戏时,旁边则是明媚光亮的白色墙体,透过墙体的色调变化来左右观众情绪从而达到辅助人物内心变化效果,严浩都表现出了超强的借用功力;而对于墙体之外用景最多的,是不同地方的一扇扇门,两者互相结合,对于人物对于命运的选择以及在苍凉世间形成的自我保护意识有了非常视觉化的隐喻。
作为新浪潮时期的左派导演,严浩更懂得将视野拓展到更为宏观的家园情怀之上,电影讲述疍家人布华泉如何从一个渔夫之子成为英国公司第一个华人大班,其中交代的时代背景本身就具有史诗电影的潜质,但严浩并未将其按照传统史诗电影手法来拍,他可谓另辟蹊径着重交代了布华泉对于身体中中英血统夹杂的矛盾和纠结,多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和主观视角去表现英属香港这一遗留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