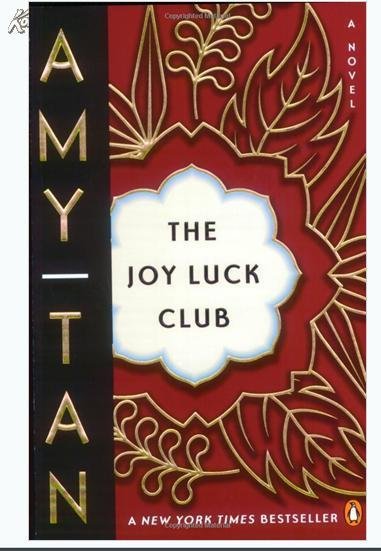张嘉译饰演的法比是剧里最不让人紧张的人物,他的几次落泪却都带着我一起落泪。黄志忠饰演的孟繁明则完全通过神态表情超脱了角色本身,一个父亲的焦虑、挣扎、绝望则让观众无法轻易冠之“汉奸”之名。
戴涛,这个老胡只断断续续拍了十天的角色给了我远超预期的惊喜。诚然,现在的我会期待他的每一部作品,会看新戏较之过往有何改变、突破,会关注作品给他带来的影响,倒较少对角色本身有太热切的期盼。从审美角度而言,战火、屠杀背景所注定的灰头土脸伤效妆必然使外貌协会成员的期待值打折扣。硬汉、血性、牺牲是我为戴教官设想的一切,但让真正打动我的是他的温柔、羞涩。
胡歌赋予了戴涛最硬气的温柔。战争使这个本该最阳光最闪耀的年轻军官展现在观众前的每一面都是支离破碎的:支离破碎的家庭、支离破碎的爱情、支离破碎的命运走向。日寇的炮火轰塌了南京的城墙,教堂的矮墙挡不住蠢蠢欲动的贼寇,挡在地狱与人间之间的不是那面美国国旗,而是戴教官守护的身躯,他面对着修罗地狱,把坚实可靠的后背面向孩子、女人。
大概戴涛自己也习惯这种军人铁血,他本身与军人无关的特质在命运把他推到伤员、女性、孩子时才有所流露。玉墨要替他脱衣换药,他瞬间脸红,局促的让人不相信这是刚刚那个果敢的战士,猛然发现他自己也还是个连男女之情都不曾接触过的大男孩。书娟拍他包扎伤口,他笑着说:“帮我个忙呗,转过头,别看。”坚韧和一点点调皮都包涵进了一个大哥哥对小女孩的细腻的温柔中。这时他不再是个模板似的热血狙击手,不在是“穿着军装扛着枪的胡歌”,他是硬气又温柔的兄长、稳重中还留存着羞涩的初尝情爱的少年、军人家庭长成军校毕业的骄傲又自尊的军官。他是戴涛,独一无二。当我们都清楚这种“人”的美好注定烟消云散,“金陵城中最炽烈的光”注定要被黑暗湮没,一个守护者注定要挡在弱者前直到粉身碎骨,又怎么能不为这以秒计时、随时都可能到来的虐杀揪心、痛苦?
看过《四十九日祭》的原著《金陵十三钗》和张艺谋的同名电影,都是以女性视角主要展现女性形象,电影的男性形象重头则是外国“神父”。《四十九日祭》最让我欣赏的一点是将神父由外国人转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将依靠国际援助的被动“他救”转化国人主动的自救,使“民族自救”这个主题的分量极大提升。
《四十九日祭》的男性角色各个都超出我想象的出彩,人物的设定与演员的演绎相得益彰,甚至于使秦淮脂粉香在这个民族的男人的韧性与血性前黯然失色。当年明月说过这样一段话:“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的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四十九日祭》把这个民族的男性的骨子里的坚韧刻画的淋漓尽致:面对外来侵略悍然抵抗,面对对弱者(女人孩子)尽力保护,甚至不惜以命相搏。那个喜欢顺手牵羊吊儿郎当的冒牌神父法比全力护着女学生,竭尽了他所有的小聪明和勇气;那个说要连尸体都不留给日寇的戴教官为了所有人放弃反抗直面最屈辱的虐杀;那个呆板懦弱的儒生孟繁明可以为了女儿把自尊踩在脚下,艰难的徘徊在道德的底线;那个最会保全自己的川军李全友磨了刀子要和日寇拼命;那个在南京城放高利贷、横行霸道了一辈子的沈老大伸手搭救同胞,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这些小人物,在不可抗拒的历史、倾颓百年的国运、凶煞至极的日寇面前,渺小如尘埃,却以最大的坚韧或挺身而上、或英勇献身,在这个以被贼寇的淫笑、死难者的哭喊充斥的城市里,发出了反抗的呼喊,掷地有声,字字以血写就。面对远强于自身的力量,人们被迫弯曲,而坚韧使他们不被折断,在这个由男人身躯构成的拱形壁垒中,保护着女人、孩子——一个民族就此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