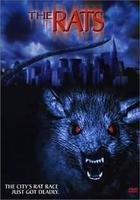《五月愚人》(MayFool,1989,法国,导演路易•马勒)餐桌——圣坛法国电影最多的场景:围桌喝酒吃饭加说个没完,喝葡萄酒比吃的菜多,说的话又比喝的酒多。对于法国人来说,与其说教堂,不过说餐桌是他们的圣坛,法兰西思想的发源。候麦、戈达等等的小资电影里,男女主人公常常是坐在桌边,咖啡,红酒,甜点,以及絮语,逸致,闲情。 餐桌当然更是法国家庭的一个中心场景。讲法国家庭的电影里,餐桌场面绝不会漏掉。《我父亲的光荣》、《我母亲的城堡》、《乡下的星期天》,都是写上世纪初一战之前法国生活的怀旧电影。里面的中产阶级家庭周末假日坐火车到乡下度假,一家人围桌而坐,旧日的好时光。
到了路易•马勒的《五月愚人》,已是世纪中的革命时代,但连观照革命都离不了“请客吃饭”。影片开头,代表传统余韵的外省老奶奶在1968年五月风暴的广播声中去世——她去世前正在厨房里切洋葱准备午饭。住在城里的子女们来参加葬礼,一场在五月风暴背景下的家庭聚会构成影片的故事,而1989年拍的这部电影对五月革命风暴的表现采取了这样一个视角,聪明而又有趣,带着一种尘埃落定之后的跳脱的审视,对法国中产阶级家庭——好的,坏的,都带着一丝微笑的宽和的嘲讽,这其中食也是若隐若现的情节。老太太去世,儿子米卢挺难过,午餐是一盘面和一瓶红酒,可是几乎未动,他心情不好。接下来女儿孙女等人都回来了,这是个殷实人家,有房产有地产,喝红酒吃牛骨髓抹面包。可是这样的晚餐桌上,老太太尸骨未寒,自私的孙女就带头争论起怎么分遗产的问题,搞的老太太儿子又没吃好。第二天,他带小孩子们去溪水里捉虾,第二天的晚餐就是煮虾,米卢说话之间还记得嘱咐“别忘了放醋!”他跟母亲一直住在乡下,对传统仍很坚持,也不愿把房子卖掉。至于念念不忘奶奶遗产的孙女,最先下手的除了首饰也是——一套套的餐具。
广播里不断播送着革命风暴已造成了经济瘫痪,汽油食物价格都在上涨。夜里因为商店关门交通堵塞,一家人快断顿了。革命派的侄子搭一辆运西班牙番茄的卡车出现,原来通往巴黎的路堵了,卡车也去不了巴黎,司机索性把番茄发给村民。米卢一家也因为殡仪馆关门,办不成葬礼,索性在草地上野餐,大嚼有“爱的苹果”之称的西班牙番茄,吃樱桃奶油派,分享大麻,话题也转为轻松,聊起女性高潮性自由来了。这无疑是六十年代的景象——自由的爱与性拯救一切,草地上的野餐,西班牙番茄,都带代表了五月风暴大派对的兴高采烈的一面。米卢跟弟媳在酒窖里共享红酒也传递着调情与好感;而米卢的女儿则跟青梅竹马时代的恋人跑到顶楼取鸡蛋,重续旧情;米卢的未婚的妹妹带来的是个女朋友,这女朋友却跟米卢的侄子在草地上快要结成“革命战友”,准备第二天赶去巴黎投入运动……空气中处处是浪漫与性的气息,不过很快米卢一家的情绪又转为低潮,因为听说革命是要打倒资本家,而米卢家怎么说也算个地主。一家人害怕起来,躲到林子里。幸而邻居还带了一只烤羊腿,可是还没吃完就因为听见有人来而落荒而逃了!烤羊腿是法国经典大菜,它被扔在草地上的情形代表着革命风暴对传统体制的冲击,而西班牙番茄则代表着革命带来的自由解放气息。 革命风暴平息之后,大家又各自回到自己生活中去。但是各自离去之时,米卢捉虾的小溪里,流进了工厂排出的污水——资本家不但没被推翻,还更猖獗了。路易•米卢写出了对五月风暴的复杂情感,伴着烤羊腿红番茄,成为法国记忆里难忘的一番滋味。
《饮食男女》、《满汉全席》、《厨房》、《油炸绿番茄》、《青木瓜的芳香》、《绿茶泡饭的滋味》、《草莓与巧克力》、《巧克力》、《火腿,火腿》、《蘑菇》, 还不要提那些不算饮食电影但是中有“吃戏”垂名青史为影迷乐道的:英国小说名著改编《汤姆•琼斯》里男主角面对情欲对象一场狂吞生蚝的以食写性;西科塞斯的黑帮片《盗亦有道》中黑社会老大在监狱里全套家伙制作意大利料理的极端粗汉与极端细腻的对比;《当哈里遇上萨莉》里男女主角在一顿普通午餐上讨论女性高潮,萨莉为了说明论点当场来了一段伪高潮,表演完了若无其事马上嚼起三明治,临桌老太却想点能让她爽成那样的菜……电影号称第七艺术,美食号称第八艺术,把这两个跟艺术沾边又跟其他很多东西沾边的玩艺弄到一块,出好玩事当然不奇怪。电影中用食物作隐喻说事也举不胜举,一会子是宗教,一会子是社会仪式,一会子是性,一会子是身份归属感……《芭比特的盛宴》(Babette’sFeast,1987,丹麦,导演加布里埃尔•阿克塞尔)法国大餐vs清教极端《芭比特的盛宴》里,最先登场,令人难忘的却不是美味而是“乏味”:咸鱼粥,还真没吃过,不过看上去听起来都让人食欲大降。干咸鱼泡一小时,刮下鱼肉,黑小麦面包加麦酒泡一小时,面糊与咸鱼末一起煮成糊,是为咸鱼粥。
遥远的丹麦清教小岛上,一对虔诚的老姐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以此为主餐,她们自己吃,也送给老弱信徒吃。老姐妹在美丽的青春时代,因牧师父亲的引导,拒绝了世俗的幸福,献身宗教,日复一日过着咸鱼粥一样简单的生活。但是,整天吃咸鱼粥的信徒们虽然在一起祈祷信奉上帝,可是却越来越不融洽,时常口角,离上帝不是更近而是渐远。 一个风雨之夜,法国女子芭比特神秘出现,恳求老姐妹收留,从此担任起做咸鱼粥的任务。直到有一天,她在法国买的彩票中了一笔奖金——看到这里,我们在一旁看的人恨不得喊,快走吧!离开这个乏味的地方。可是芭比特却没有走,她要为老姐妹和她们的信徒做一顿真正的法国大餐。 活龟活鹌鹑,从法国特购运来,现杀现制,可以想见把两位教徒姐妹吓得够呛,简直是魔鬼的食物啊,搞得什么名堂!但是当晚宴开始,信徒们从游移陌生,到味蕾逐渐被美味击中,他们心情逐渐放松,线条逐渐柔和,几杯酒下肚,互相还道起歉来。这晚,一个当年追求过姐妹之一的将军也来参加晚宴,只有他最懂这顿晚宴的价值。他回忆说,很久以前,他在巴黎曾经参加过一场宴会,也吃过一道同样的菜,那位厨师是一位女性,她的本领是做出的菜具有爱情的灵效……这里说的是宴会,当然其实也是在讲宗教人生。“咸鱼粥”——枯竭、无创造力的生活与想象;而芭比特的盛宴——生活的丰富,在“魔鬼食品”的诱惑前,僵硬的心灵软化,他们感受到温暖人性。所以,芭比特的盛宴就是感官的盛宴,人性的盛宴,一味压抑感官的乐趣而追求纯粹的精神,其实可能势得其反。
《芭比特的盛宴》是丹麦女作家丹尼森(《走出非洲》)写的一个故事,电影中的那顿法国菜盛宴在电影流行之时曾有餐馆依样推出。晚宴的菜单是:开胃酒:Amontillado雪利酒,前菜:海龟汤(ConsommeofTurtle);俄国小薄饼(BlinisDemidoff)抹Demidoff鱼子酱,配1860年VeuveCliquot香槟。主菜:鹌鹑千层酥盒(QuailenSarcophage),配1845年波茛地红酒ClotVougeot;沙拉。甜点:糖渍水果佐朗姆酒蛋糕;新鲜水果。饭后酒:干邑。咖啡或茶。 至今在美国,高级餐馆中仍以法国餐馆最贵。雪利酒是葡萄酿的烈型酒,读海明威之类小说常常见到,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今日正式的法国套餐,大致仍是上述的程序,但开胃酒也可以是白葡萄。到餐馆落座之后可以不看酒单先每人要一杯白葡萄酒,每家餐馆都有所谓housewine,就是说如果你不报名让餐馆给你上的酒。喝着这杯白葡萄酒,然后可以点菜,点好主菜之后,再拿酒单配酒。主要原则是白葡萄酒配海鲜鸡肉等白肉,红葡萄酒配牛肉羊肉等红肉。口味越重的菜,酒也要越浓。主菜吃完之后,侍者会再拿点心单,也有专门配点心的葡萄甜酒,但今人一般都只喝咖啡或茶了。
西餐正式餐桌桌子中间不是摆菜,而是摆花、蜡烛等装饰,菜分到每人的盘子中。其实比中餐品种少,但法国菜跟葡萄酒文化分不开,强调不同的菜配不同的酒,加强各自的美味,所以一道高级宴会不光要看菜,还要看酒是否配得合适。《芭比特的盛宴》里,就对芭比特选的酒有重点介绍,以当时的运输条件,从产地运到小岛而保存完好就所费不赀,什么时候上什么酒,用什么杯子,芭比特都要对临时找来帮工的小厮仔细叮嘱,而席中美食家的将军光是从小厮上酒的规矩就已经知道今天厨房中不是等闲之人。 芭比特菜单中的几种原料,即使是现在的美国人也不是家常吃食,所以《芭比特盛宴》中的孤岛其实并不孤。
要按该片的说法,可以开玩笑说美国人和中东人打仗实在是双方都吃的太差——不是说吃不饱,而是吃得不好。而恰恰现在带头反对美国去打仗的法国人,至今仍是西餐世界中的权威人物。清教徒传统下的美国,一般大众的口味虽在不断进步,但至今还很狭隘。不要说别人,端碗乌龟汤给布什,他可能也象片中的老姐妹那样心惊肉跳。一般美国人还是只懂得吃牛羊肉,不象法国馆子里鹌鹑蜗牛鸭子什么的。其实法国菜里也吃牛肉鸡肉,但是《芭比特的盛宴》作者拟的这个菜单,特地要挑那些清教徒不吃的东西,强调的就是两种观念的差异。而法国菜对红酒的重视,在这里具有象征意义,因为红酒从希腊文明起就代表了感官与本能,日神阿波罗与酒神狄俄尼斯象征着西方文明中理性与感性的二元,也是秩序与创造的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