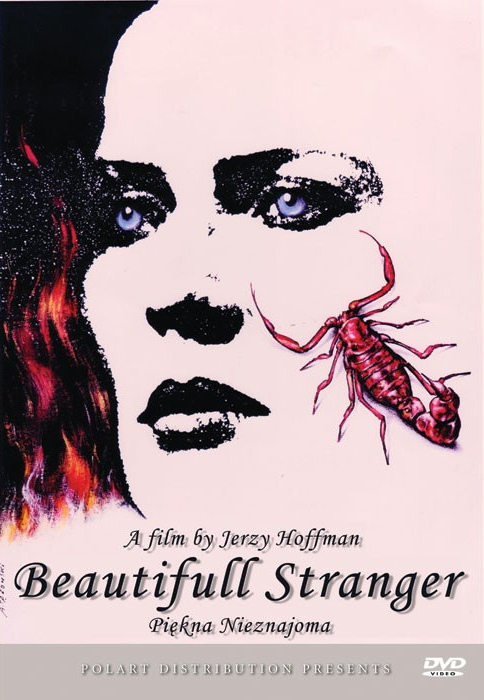我个人认为,电影之所以受欢迎,不仅仅是因为其场面宏大,制作精良,很大程度也在于电影拥有极大的发挥空间。在电影的世界里,短短的一到两个小时,它可以为你构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人们对于迂回也是比较感兴趣:战场上的迂回战术,官场上的迂回战术,看小说喜欢回环往复的,讲价的时候绕圈,等等。迂回有时可以绕开主要矛盾,比如电影中绕开了国与国的紧张关系,更可以运用于生活中。有一个广告的例子,现在的广告可不会直直白白地说我们这产品多么多么好,而是一定要先问问题,再做对比,最后送东西,最后的最后你就买了。
看这电影,每个人都想到了许多触类旁通但又似是而非的东西。可见,文艺作品拿梦境和心理学说事,大家都有过不少经验。《机器猫》多让孩子们喜闻乐见的题材,也拿做梦枕头套过三重梦境。博尔赫斯大半辈子都在各类神秘几何图形的结构下写梦啊镜子啊迷宫啊之类,而且他随便往前一追溯,远到《一千零一夜》里各类玄幻结构,近到诸位宗教界人士的冥想宇宙结构,说明许多人都没事动过“现实世界是否一场梦”之类的念头。科幻小说的例子就不多提了。其实何需文艺作品来武装,随便找个朋友聊天,他也许都会跟你念叨些类似念头。
其实电影自身的创意并不局限于形式、表现手法的创意,电影也是有《灵魂》的创造物,它一直在尝试给我们传达《思想》,而电影中的这些《思想》的《创意》,也是电影创意不可缺少的一环。我看过不少电影,但是自己主动看《第二次》的电影只有《海上钢琴师》,并没有像是大片一样恢弘的场面,在表现手法上充其量也是倒叙插叙相结合。
《嫌疑犯X的献身》部电影首先告诉了观众谁是凶手,需要推理出来的是证据。这种在推理上类似倒序的方法创新了大部分推理影视所遵循的“谁是凶手”格式;推理剧发展顺序往往是被害人遇害——主角侦查——找出凶手——破案。我们很少想过被害人会“有假”,但这部电影中被害人偏偏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个人,被害人不成立,遇害时间不成立,无论怎样侦查都无法掌握嫌疑人犯案的证据。
在老师推荐的著作《创意,是一笔灵魂交易》中,作者朱莉娅·卡梅伦提到过两个修复创造性自我的工具,其中之一便是“艺术家之约”。所谓“艺术家之约”,就是每周要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买些小玩意儿,让自己保持一颗创意的心。我觉得,创意并不一定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能被激发、被表现。一个整天沉迷于手机电脑的人,又怎会生出好的创意?好的创意来源于生活,来自于情感的碰撞交流。我们要学会发现创意的需要,也就自然能够产生好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