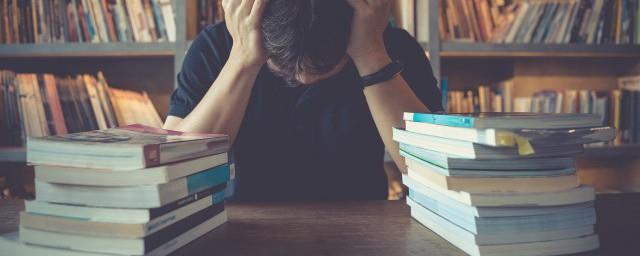影片开头极美。房间、家具漂浮,像浸泡在海水中,整体是清冷的浅绿。这一冷色调蔓延到艾丽萨的大衣、发箍、工作服,科研基地的墙壁、仪器、办公桌,就连邻居买的蛋糕,上面也点缀绿色的柠檬,大反派斯特里克兰德买的车也是“水鸭色”。只有当艾丽萨心底有爱意萌动时,冰冷消退,暖色入侵,头上的发箍、脚上的鞋子,变成红色。导演陀螺拍出过《潘神的迷宫》,他当然知道美学上的松与紧,对观众意味着什么。他也当然知道,电影需要有明确的呈现,也需要有模糊的表述。这些模糊之处,是予以观众的自由。观众看电影都是看自己,学识、经历、性格等等都借由这一模糊地带,参与到重新创作这部电影里。很多电影可以在影史上一直丰饶,即源于在生活的暗示下,观众连绵不绝的再创作。《水形物语》偏不。它就是要将所有的元素都坦露在外,将所有的边框,都勾勒清晰。任何再解读的企图,在这里都失去了落脚之地。导演陀螺用美学囚禁了观众。就像一出门,刚刚还在邻居沙发上用脚跳舞的艾丽萨,马上就成为一个胆怯、畏缩的清洁女工一样。电影用镜头成功临摹了一个和影片中1960年代一样施予压迫感的背景。
影片告诉我们,所谓怪物,可能是你还没有找到你爱的人,走到你适合的环境。艾丽萨颈上的抓痕,到水里,变成腮。她和她爱的鱼人拥抱、游走的画面,是我看到的2017年最温暖的镜头之一。这一定是一部两极化的电影。坦白的恶趣味、无辜的黑暗面、美丽的邪恶、粘稠的性感、肮脏的纯洁,反人类的温柔。影片一直在逼迫观众反省自己,到底是人形的怪物还是怪物形状的人。你看到怪物,还是自己才是那个怪物。《水形物语》柔软的躯体里,含有一根坚硬的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那么坦诚。
这个片的点子其实来自于陀螺的一个小说合著作者Daniel Kraus。他有一次吃早餐的时候和陀螺分享了这个想法,当时就引起了后者的极大兴趣。但实际过了好几年才开始制作这部电影。而Kraus坚持把这个点子写成小说,于2018年2月28日面世。他俩创作时不停交换意见,但算是各自独立创作的。所以小说并非电影的直接改写,有电影里没有的情节,比如抓捕两栖人的过程。
本片也被看作是另类版的“美女与野兽”,但导演并不喜欢美女与野兽或是青蛙王子里野兽变成人的桥段。他觉得真爱在于理解和接受,而不是转变。而且导演并没有把这个故事看作跨物种恋爱,他觉得对方是一个水元素之神,而非B级片怪物。
我认为《水形物语》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拥有非常丰富的质感,表面上是一个童话故事,再往下深挖是一个比较重口味的现实主义成人童话,然后你看到最后发现它虽然重口,但是有一个和普通童话故事一样简单美好的内核。
人鱼(兽)恋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母题了。星爷的《美人鱼》似乎还没过去多久(实则也只是去年春节档的片),又一部讲人鱼恋的片子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并最后把金狮捧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