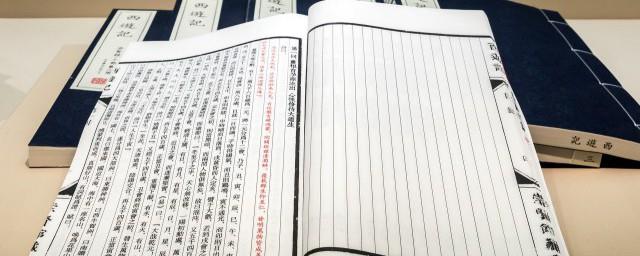初读围城大约十四五岁,是那个少女怀春,少男钟情的年龄。一度爱不释手,前后买了四个版本(包括一个盗版),那时虽读了十来遍却仍像方鸿渐一样无法理解为什么董斜川这么一个青年英派的海归外交家,娶得美妇,却爱作旧诗,一会什么未许避人思避世,且扶残醉赏残花,一会什么何需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枉然...,一幅前朝遗老遗少的做派。大感兴味之余把董斜川推崇的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找出来读,虽然无感却发现此人是清华四导师之一陈寅恪的父亲…。读了围城意犹未尽,可是钱钟书再无别的小说,于是便从七缀集开始,又读了谈艺录,管锥编,还好本科的专业是中文,有段时间一边啃王力的古代汉语,一边看管锥编。总之循着围城看了不少书,他本人的,他父亲的,还有他那位族叔钱穆的。如今围城已有十几年没读了,今后或许也不会再读,不过某些段落或词句已经溶进记忆了。以学者创作小说的似乎不多,固然小说比学术论文要容易读的多,然而学者写的小说未必不如文学家的小说——至少我觉得围城比二马要有趣许多
钱钟书先生真是极可爱的人,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他的博学和幽默。这本书有趣,也只有钱钟书能写出这样一群人物:国破家亡的年月里,尚能保持优雅的书生。骨子里流淌的风度,简直就是奢侈品。掉书袋也好,引经据典也好,一个读书人骨子里的干净和纯粹,那种浑然天成的优雅气质和无所谓的态度,却不是心怀杂念的人能够比得了的。不管是第一次,还是以前看过,《围城》都适合在清闲时候,半躺在沙发上,悠然品读。读不读得懂,与有没有文化无关。别急,也许你还需要更多的人生阅历。会心一笑时,别忘了抿一口淡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校园内流行看小说《围城》,校园外万人空巷看电视剧《渴望》,一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我也买了《围城》来看,一下就被幽默的语言文字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吸引了,也许是因为从小到大都身处校园,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了解更多,另一方面又即将毕业走向社会,对进出围城有着莫名的期待与徬徨,总之对这部小说爱不释手。后来陈道明主演的同名电视剧播出,深深感叹对原著的诠释十分到位,尤其是陈道明对方鸿渐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或者说陈道明本身就是现实版的方鸿渐,百看不厌。
《围城》,是我在看过电视剧以后才去读的一本书,一本小说。不得不得承认,小说中作者的语言是最大的亮点,极尽调侃之能是。主人公方鸿渐也不能逃脱,而书中所有的人物都在被调侃之列吗?肯定不是,唐晓芙就是个例外。尽管我本人在看电视剧和小说时,并未有对唐晓芙这一角色有多大的喜欢和欣赏,但作者确实没有调侃她,而是比较得意的一个人物。为什么会如此?当我了解了作者的一些情况后,才知道出乎天然的东西才是美丽的,可爱的,于是,唐晓芙这一角色就是天然的,没有心机的,比较纯一些。也因为如此,唐晓芙才得以幸免。
刚读完第二遍,看完《围城》电视剧之后,搁了几年的重读《围城》的想法终于成为做法。第一次读它,喜欢的是钱钟书爆炸式的文才,最爱读他的那些文采斐然的“譬如”、力透纸背的讽刺、入木三分的分析。时隔几年,见识了电视剧,又回味一遍小说,惊叹他的文才之外,又有一种新的感想,使我对钱老的景仰之情又添一分。重读之后,可能是自身近几年经历和阅历的成长,让我对那些精彩的句子多多少少消减了一些喜好,反而偏爱起这故事,这情节,这感情来。
《围城》是我大学时就读过的一本印象深刻的书,是钱钟书先生写的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没看过的人不一定看得下去,而看过的人,内心底,必然会掀起些许波澜。时间久远,很多文字细节均已忘记,连故事情节也只是模糊的大概,但我却记得这样一段话:"工作是妥协,生活也是妥协,婚姻更是妥协,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妥协,这是每个人的命运,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