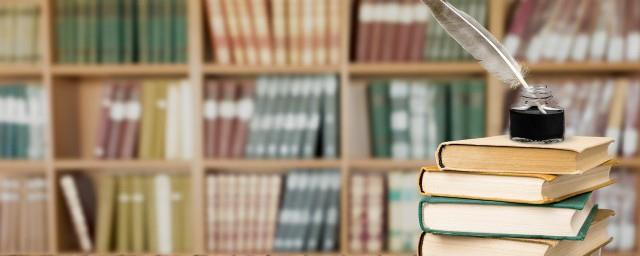艺术品市场不健全。两次工业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暴发户成为贵族,而新贵族一直以来都对旧有的艺术体制不买账。虽然你明确知道他们要的绝不是原来搞的那一套,但是你很难猜出那批暴发户到底要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新兴市场,艺术品正在商品化,并逐渐成为投资品;艺术品交易从过去接受订单,变成直接进入市场交易;针对新客户的涌现,交易模式出现分化,官方展览不再是唯一的交易平台,画廊和艺术经纪人的出现激活了这个新市场,同时也加大了投资交易风险。在梵高和弟弟提奥的通信中,我们能明显看出当时的艺术市场焦虑,主要是因为没有人能为新艺术背书。但在今天,艺术品市场不但成熟还有很多细分市场,艺术家的筛选和晋升有相对多样化的管道,因此19世纪中后期的问题就完全不存在了。
落后的通讯技术。20世纪以来,电话、电视、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普及使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艺术家遇见伯乐的机会也越来越大,换言之,艺术家成名的机会也逐渐增多。正如贡布里希所言,不是艺术批评家们没有准备好接受新艺术,而是新艺术几乎难以传到批评家那里。尤其像高更这样躲在偏僻岛屿作威作福的土霸王,虽然常常把作品寄回欧洲,但因为本人缺席,也很难在欧洲艺术界打开局面。所以,落后的通讯技术使艺术家成名的成本要比当下高得多,批评家和理论家错失优秀艺术家的概率也大得多。
为什么有才的人往往很惨呢,因为他们经历的事情对啊,见过的人情冷暖更多,心中的悲愤与不甘,伤心与无奈更多,但如果仅仅用语言来表达那是很片面的,就必须要用比白话更深层的东西来表达了,想的越多,创作的越多,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创作者的想法集合。
艺术理论不完善。没有人能为新艺术背书的原因是出自第一点,也就是通讯技术过于落后:学术界难以消化新的艺术,也难以形成对新艺术的讨论,其表现就是艺术理论不完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现象不应该完全让保守主义背锅,通讯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人们会自觉的选取悲情艺术家消费,就像流行歌曲会着重描写失恋一样。不能说一个很有钱或者很有权,出了一些问题就是“悲情”,诸葛亮悲情吗?他也是非常厉害的艺术家,我觉得也许非常悲情吧。
现实的枷锁无法困住这个人的思想,不疯魔不成活,所以有些认识甚至是超前的,有先锋性的。但是越是这样的越和社会格格不入,现实让他们难受,社会也很难接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