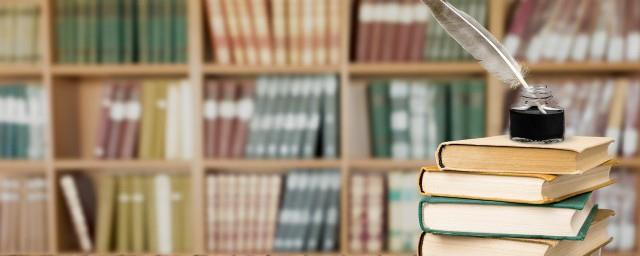文学的艺术性,取决于人的灵性与艺术家的天赋。因为,文学的概括是狭义的人文学术;广义上也包括悲惨的人生,包罗万象莫衷一是。文学的艺术性不取决于其悲剧性,文学的艺术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悲剧性。
悲剧性不能等同于艺术性,但是悲剧性往往可以引发人类的各种的共鸣,进而散发出强烈的艺术效果――因为克服悲剧这件事,是人生的常态。悲剧确实在等级上高于喜剧。如果说幸福和美好是某种意义上的平衡,那么悲剧就是那些试图打破平衡的情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就是一场悲欢离合的剧目,结尾都是自己的死亡和周围人的死亡。我们笑过爱过开心过,却最终都会成为过眼云烟。对个人来说,这就是一种悲剧。但是,即使是悲剧,并不代表我们就不向往爱,不向往欢乐,不向往美丽,不向往平衡;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对美好追求的过程。我们希望在人生中追求美好,以给死亡这个最终悲剧赋予一个优雅从容的姿态。
本人不专业,只是曾经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都知道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呢是个哲学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反复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生活本身就是悲剧!我们在笑脸和欢迎声中诞生,而在寂寞和痛哭声中离去,对于大多数普通人的人生来说,都是从年少时的希望和梦想走向年老时的麻木和无奈的,所以,悲剧更能倒映出一个成年人的心情和思想。
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性在文学中的体现或许是源于叙述的真实,或许是源于议论的精辟。然而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艺术性和现实意义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对于文学,因此悲剧往往比喜剧更容易抓住人的内心,更容易产生现实意义和价值,因此你的感性认知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如此,“喜剧的内核往往是悲剧”,这也是常见的一种评论。但是并不能因此将艺术性与悲剧性关联起来。
悲剧性的文学作品,就是表现这种输掉的情况的。主人公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悲剧,无论他是英雄还是小偷,男人还是女人,国王还是文人,任他有移山填海的力量,都无法避免地走向悲剧。这样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进行酒神宣泄的场景。我们的本能心绪被调动起来,跟着书中人物大喜大悲,心灵被深深地撞击和碾碎。我们悲伤不已,为主人公的遭遇而慨叹。喜剧本身就是平衡的。我们只有在开心的时候欣赏喜剧(比如春节过年或者祝寿现场),才能避免喜剧带来的过于完美而让自己产生失落感。我对尼采的“酒神”“日神”的理解就是这样了。酒神用本能和狂喜忘掉悲剧,而日神则试图接住酒神产生的各种问题。但是由于没有读过《悲剧的诞生》,我只能领会到这一层了。
想艺术,悲剧方向更好努力。用生活讲理想和用美讲梦想都能达成伟大的艺术。前者有现成的生活经验当土壤,作者勤观察多思考,找到自己的那块地深耕,艺术性是够得着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展现在作品里,旁观起来就有点儿悲剧色彩。用美当工具更依赖天分,偏偏这些天才里只有极少数偏爱规整有完满的那类美,所以我们看到的“艺术的”大多是“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