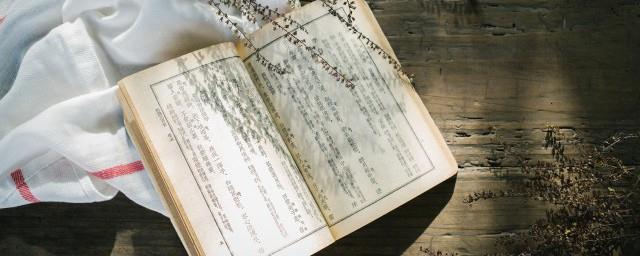鲁迅很爱他的同志。比如女师大刘和珍牺牲了,他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对这个女子表示深切的哀悼。左联五烈士中的柔石、白莽都是鲁迅的朋友,他们倒在了国民党的屠刀下,鲁迅感到很震惊,他一面躲避起来,一面救济柔石的遗孤,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写《为了忘却的纪念》,把柔石等人的事迹宣扬出去。他还写一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都体现了他的一往情深。
鲁迅是一个“生活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鲁迅,会了解很多。鲁迅似乎只对呼吸、对活着这一件事情——作为生活者的一个最后底线和感觉——从不怀疑。借用日本学者竹内好的说法就是:鲁迅是一个诚实的生活者。他的建立在个人性上的“生”的感受赋予其穿透事物表象的能力。个人性的“生”的感受简直就是其思想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这也是同鲁迅早年个人悲苦的生活经历有关,是对个人生存的恐惧和艰难的深刻体认。
看过太多关于鲁迅的评论,有赞誉的,有批判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无法堵住部分人的“破口大骂”,更不能也不会压迫大多数人的赞誉美词,有的只是自己的观点,对鲁迅的那点想法,决不是像以上两者的那种偏颇的绝对的观点。向来坚持用马克思的“两点论,两分法”去看待任何事情,不论是鲁迅这位文坛大家,还是对待生活的点滴小事,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
不服的人,有好人堆里的坏人,坏人堆里的坏人。以鲁迅先生文学成就,历史地位,百年前后无人超越的高度,任何攻击和诋毁都无损泰山之一毫。我们只有高山仰止的份。虫豸们不遗余力,要打倒这面民族精神旗帜,它们有可能达到目的,它们一旦达到目的,就是民族深陷灾难之时。鲁迅先生高风亮节,胸怀博大,他希望自己“速朽”,用自己的“速朽”,换来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是,恐怕先生的一厢情愿,难以实现,因为,先生并没有从我们的视线里逝去。
鲁迅对于社会底层有发自内心的爱,比如闰土,这个儿时的玩伴,多年后重逢,叫鲁迅老爷。鲁迅十分同情他,说:“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又比如长妈妈,这个粗笨的保姆,睡觉的时候张开一个大字,为少年鲁迅所讨厌,但他为鲁迅买了一本带插图的《山海经》。30多年后,鲁迅写文章纪念她。文章末尾说:“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鲁迅很爱亲人。鲁迅小时候,他父亲病重要死了,邻居衍太太说,你赶快喊,于是鲁迅使劲喊。他父亲微弱的说,有什么事儿啊,不要喊。后来鲁迅学了西医,才知道一个人临终的时候,要让他安安静静的去。所以他对这件事十分后悔。他父亲去世30年后,他写了《父亲的病》,里面说:“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