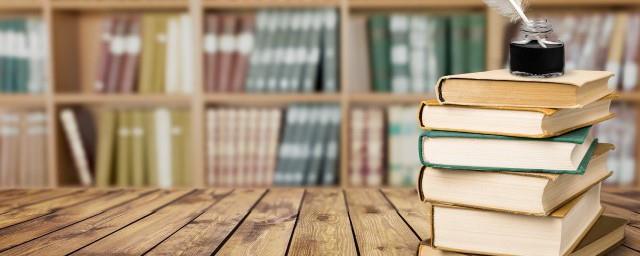在刘震云看来,话剧《一句顶一万句》从心事入手,将那些怀揣心事却永远无处诉说的人的声音在舞台上放大。“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被译成了20多种语言,不同国家的评论家对这部作品共同的评价是,认为‘其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肺腑之言’。这肺腑之言与老百姓的日常琐事有关,对说话人而言就是天大的事情。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的视野非常宏大,剧中的思想认识点、转折点,以及整个框架、结构,完全是牟森的人物结构、故事走向、情感结构,对我非常有冲击力。牟森就是想把被忽略的人的情感、心事、肺腑之言,搬到舞台上告诉大家。”
这是作者的一种信仰,正像书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老詹那样,一辈子传教,发展信徒,虽然处处碰壁,但他心中始终带着顽强的信念和对虔诚的光的向往。在书中,吴摩西一直珍藏着詹牧师的教堂草稿图,正是这福草稿图点亮了牛爱国的人生,让他看到了自己的纠结所在,于是他要抛弃繁琐的人生纠结,彻底彻悟,终于决议按照自己的人生信义来生存。
《一句顶一万句》里,当我看到吴縻西丢了女儿巧玲那一段,夜深了我也睡着了。梦里老牵挂走丢了的巧玲,又迷迷糊糊我把女儿丢了,也分不清我是在满世界帮吴摩西找巧玲还是找自己女儿。一晚上东奔西走,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口干舌燥的。醒来后接茬又看,当看到巧玲成为了牛爱国的妈,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最感动的应该是教书的老汪,他女儿灯盏淹死在了水缸里,孩子死时老汪没哭,过了几个月后老汪整理物品时无意中看到一块糕,糕上有一排牙痕,是她女儿生前偷吃时留下的,还被老汪骂了一顿。看着这排小小的压痕,老汪嚎啕大哭。
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同样一句话,两种说法,她拣的是好听的那一面,坏话也让她说成了好话;同样一句话,两种说法,她拣的是难听的那一面,好话也让她说成了坏话。
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吴摩西和吴香香冷战时,吴摩西离开家跑到外面,巧玲克服自己的恐惧跑到棉花货栈去找吴摩西喊他回家。看完这段感觉真好喜欢巧玲这个人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