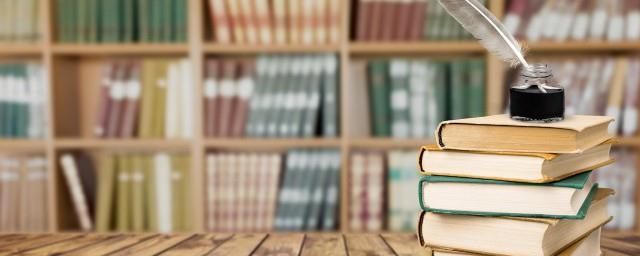《活着》最大的意义在于,人生在世,最勇敢最坚强的事,就是活下去。这是我看过的最坚强最励志的小说,没有之一。富贵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特别是成年之后是卑贱到尘埃里的人,他的一生,虽然称不上波澜壮阔,但绝对是跌宕起伏,几乎可以说是一直在往下沉,就没有上升过。从地主家的少爷,到最后茕茕孑立,和自己的老牛为伴。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的事,看过那么多的生死沉浮,他耳不聋眼不花,对自己的一生经历过的所有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
余华在《活着》中的笔法和思路没有和当时的其他作家一样进入时代共时性的常规创作,没有把精力集中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方面,也没有着力刻画在改革大潮中,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而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及人物内心在时代洪流中发生的嬗变。他的写作方式更为原始,更为真实,更接近生活的本真状态,更能以直接的方式抵达人的内心,让人震颤。
富贵贫穷,生存死亡,如不掺杂情感则只是一场轮回变化的剧。这剧是独自生长的,不迎合观众和导演的喜好,只由冰冷的上帝操控。福贵的荒诞跋扈到败家倒灶,全家人的反应并没有他和观众预想的那般激烈,母亲只叹了句“上梁不正下梁歪”而父亲则在还完债后讲了鸡变鹅,鹅变羊,羊变牛的发家史和两代败家子把鸡都败没的故事。
《活着》中的主人公们,大多没有安邦济世的崇高理想,而是面临着最残酷的生存危机,他们平静而苍白地活着。福贵一家,妻子家珍的死,是因为她的操劳过渡,她是家里的二把手,她有病了也不愿意休息,她休息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将很难解决,她带病劳动,根本没有医治的条件,直到最终卧床不起离开人世。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作者跳出自身的情感超然的写出这部著作,不带任何个人情感,他如小说开篇中第一人称的“我”,只是故事的记录者。不同的是“我”只带着耳朵,而余华只带了笔,冰冷的笔记录着故事,他如上帝般跳出轮回俯瞰着福贵的一生。
余华在序中说,他之前与现实关系紧张,一直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而后才寻得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