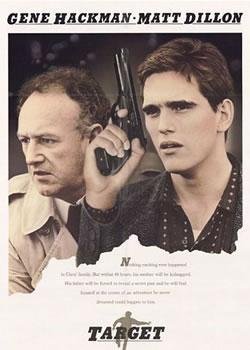《斗牛》的观影经历是让我欣喜的——终于在09年看到了一部牛B的内地电影,当然我们总是能在一部电影作品里找到前辈的影子:你可以说《斗牛》是一部喜剧版的《活着》,一部人兽版的《鬼子来了》,甚至一部中国山村版的盖·里奇。 能让我联想起这么多优秀的电影,已经说明了《斗牛》的质量。在目前还活跃的几位第六代导演中,贾樟柯只能拍拍小众艺术片,张元在吸毒前就有才尽的嫌疑,娄烨在情欲内心的挣扎里越陷越深,宁浩认准了商业类型片的路子高歌猛进,王小帅则在票房与奖项的二难选择里进退失据——相较而言,
我一直觉得管虎是一位既不缺乏人文关怀作品又不缺乏可看性的导演(当然所谓的价值意义都是被阐释出来的),事实上,能够在电视荧屏上凭借《黑洞》《冬至》《生存之民工》这些叫好又叫座的作品走入普通观众的视野,管虎的导演功力不证自明。 在以抗战为时代背景的电影中,《斗牛》巧妙的构制了一种相对于权力叙事的话语张力:对普通农民的生活来说,日寇、流民、土匪、八路、国军,乃至日后的解放军,都成了过眼云烟,在最朴素的生存理念的支配下,农民卑微而又坚韧的活着,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永远无法遮蔽农民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最后,他们还用最质朴的契约理念无情嘲笑了所谓的宏大价值——在市民社会呼之总不出的时候,《斗牛》用小农意识曲径通幽的玩了一把市民理念的宣泄。
这里也存在者另一种微妙的解构关系:荷兰奶牛是以“八路牛”的身份被神圣化的,即使全村人惨遭日寇屠戮,这头“八路牛”却安之若素,甚至成了牛二的精神寄托和唯一伴侣。而牛二在抓阄被分配到饲养“八路牛”后,老大的不情愿,
九儿(闫妮饰)在一旁高喊“要他革命”的情节显然应合了对宣传机器的教条叙述厌烦透顶的当代观众心理。九儿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她处处顶撞权威,用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在贫瘠的山村里播撒着生命的意义,然而又是一个伪反抗者——虽然她嚷过“妇女解放”之类的话,但山村封建秩序显然又庇护了她——她与牛二的婚配完全是宗族势力的利益安排,但九儿与牛二的爱情便是这样怪异而又自然的滋长起来。
最后当牛二(黄渤饰)拉着他的牛坐在土坡上感叹年华的流逝时,我立马想起了余华在《活着》里描写的那个老农和他的那头牛(可惜电影《活着》没有体现出来)。 作为农耕文明的象征,牛与农民的紧密关系不言而喻,虽然《斗牛》里把中国牛替换成了一头荷兰奶牛,但从根本上看,还是这头牛在给农民提供粮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不含三聚氢胺的正宗荷兰牛奶成了农民难得的营养保证。丰满的奶牛乳房很容易让男性农民有性的联想,于是,偷摸奶牛的奶子成了牛二的罪状,他甚至因此被戴着高帽游街。不过在管虎的处理下,游街也被戏谑化了,全然不见《芙蓉镇》式的庙堂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