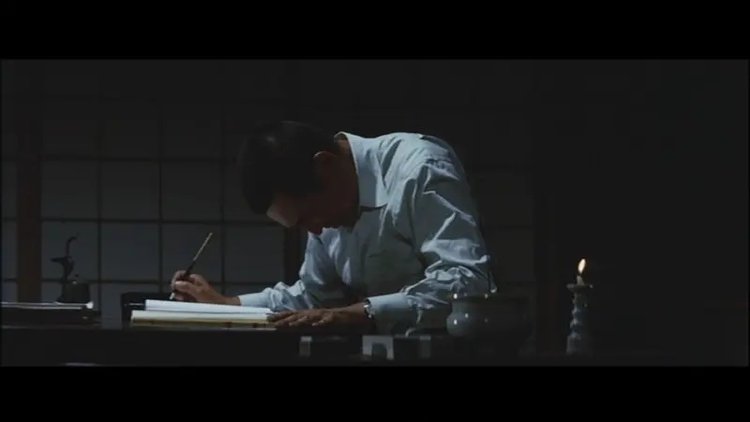在拍摄《一代宗师》时,有一场戏,是个雨天,梁朝伟走进一间茶馆,章子怡等在那里,两个人一段感情戏。拍完了之后,一旁的编剧邹静之就觉着不对,这里面没有情节的推进,对白也很少,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观众接收不到,不行,得加戏。当时王家卫就摆摆手说,“不用了,够了,都在里面了。”邹不明白,心想电影没有这么拍的,直到当天晚上,王家卫把剪好的片段拿给邹看:只见镜头缓慢的移动,拍窗外的细雨落在石板路上,拍眼神,拍嘴边的浅笑,拍若即若离的身影,只有雨声和微弱的呼吸声。想要的那种情愫,不多不少,果真全在里面了。这就是“质感”。
我们这代人基本没有经历过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身体什么都不缺,缺心眼儿的居多,现在看来,我是其一。至于精神生活,看电影是最高级最奢侈的享受。小时候跟着母亲在露天电影院看过不少电影,那时流行罗马尼亚、日本、前苏联。后来走近俱乐部,看了《芙蓉镇》和《红高粱》,验证了自己的领悟能力。如果从事了与电影有关的工作,《芙蓉镇》绝对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电影之一,也是爱上电影的开蒙和初衷,为自己心目中的好电影和观影喜好,定下了一个注重故事性的标准和基调。只可惜如今“平庸”生活,离梦想越来越远。
如果把一部电影比作一颗苹果,那么质感就是“皮”,叙事是“肉”,而观念是“核”。皮是负责诱人的,肉是用来咀嚼的,而皮干肉净后留下来的才是核。换成通俗的语言就是:“叙事”呈现故事,“观念”传递价值,“质感”营造氛围。这三者在实际的电影表现中,是彼此牵连、互相影响的。比如:若叙事不够清晰,则观念无法传达;若观念本身无趣,则叙事也一定无聊;若一味追求质感,叙事就难免会云里雾里;若叙事太满或观念太重,影片也就丧失了质感。
电影的魅力在于“体验不同的人生”。当你走进电影院,大门关上,光渐渐暗下来,仿佛与现实就隔开了一段距离。于是屏幕上发生的故事,就成了你此刻正在经历的故事。这是看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它给了我们一个“离开自我、走进别人”的机会,过他人的生活、面临他人的选择。而在故事的最后,灯光亮起,灵魂又重新回到自我。而这个我和之前的我,已经有了一点点的不一样。
回到最初的结论,一部电影,如果能把一两个维度照顾好,就可算得上优秀了。但对于一部杰出的作品,一定是在这三个维度上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点,不厚此薄彼,也不堕入平庸。这就是我的电影观,也是我对电影的一套评价体系。我还要带着它去审视更多的电影,享受电影带给我的快乐。
对于好电影,每个人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是烂片的,会有人觉得是好片,所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体会。《我能说》讲述性格耿直爱打抱不平的热血信访女士通过向极具原则性的9级公务员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逐渐学会讲英语的同时两个人的心扉也逐渐打开成为忘年之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