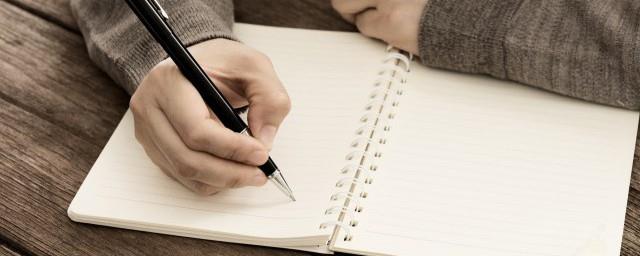1954年的奥黛丽·赫本已经拥有极大的声名,她凭1952年拍摄的《罗马假日》在这一年夺得了第26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这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与身为导演、演员、作家三职的梅尔·法利尔(Mel Ferrer)结为伉俪。当然她的声名显赫引得很多剧本铺天盖地袭来,关于二战题材的《安妮日记》被她拒绝,因为她无法忘掉童年生活中战争留下的阴影。她接拍了歌舞剧《甜姐儿》,并指名道姓要求弗雷德·阿斯坦(Fred Astaire)来担纲男主演。对于奥黛丽来说,这是一位大师级的舞蹈明星,因为从小习舞的她最大的梦想,便是与弗雷德能够同台舞蹈。在她儿子肖恩所撰的《天使在人间》一书中,他这样写道:“母亲去世以来,我在许多采访中常常被问到,我最喜欢她的哪一部电影。我真的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认为我能够充分客观地挑出我的最爱,就太可笑了。但是,我一直尝试着给一个答案,说出那些我知道她曾经为之付出了个人情感的电影。电影《甜姐儿》就是其中一部。这部电影实现了她与弗雷德跳舞的梦想。毕竟那些年来,又一次能够与她最初的挚爱——舞蹈相连,想必是一桩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这部影片融合了诸多时尚元素,片中的服饰便令人眼花缭乱,更别提百老汇舞台剧式的音乐、舞蹈……这是一部绽放奥黛丽·赫本个人风采的影片,就像章子怡从小练舞,终于在后来的武侠电影中得以 施展身手。
影片无非从一个灰头土脸的女孩子身上出发,让她的美在时尚杂志上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智慧与美貌的集合——于是杂志社的摄影师与女编辑开始了“造星计划”,让丑小鸭变成了天鹅。这期间,摄影师与女孩子相爱,相爱过程中,女孩又因为专研哲学崇拜某位哲学教授,在探讨过程中她忽然醒悟:在自己的美貌面前,教授充其量已还原为男人。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她无法不受到赤裸裸的性的侵犯,于是她跑回摄影师身边……
影片中还有一个对我来说是新名词的“移情主义”,它的创始人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洛采,提倡“物我交融”,现在已广泛运用于艺术领域,成为美学范畴的一个专业术语。而影片中显然是偷换了概念,“移情”变成了“处处站在对方立场上为对方考虑”的意思,这种套用哲学术语却将之运用到爱情情节中,显然是一个可爱的举措,借由摄影师和女编辑之口将定义改变得那样彻底,大概那些研究哲学的人要贻笑大方了。
关于那场草地上的舞蹈,奥黛丽·赫本身披婚纱与弗雷德翩翩起舞,在弗雷德的回忆录中他如此写道:“这段舞蹈需要在巴黎郊区一片美丽的草地上拍摄,因此我们一直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但是当我们抵达那儿的时候,天气糟糕透了,天天都在下雨,草地泥泞不堪……我记得奥黛丽说:‘为了和弗雷德·阿斯坦一起跳舞我已经等了20年,最后我得到了什么?一身泥巴。’我当时想,这个女孩简直太可爱了。”
赫本以她纯美的扮相赢得万千观众外,她的为人与处事风格温文尔雅,为她博得更多朋友的青睐,她拥有了人间天使般善良的心灵与funny face,所有以她为中心的影片都宣扬了“极致之美”,而这种美直接来自于“众星拱月”的力量——她要感谢的也许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上帝亲吻了一个小女孩的脸颊,于是赫本诞生了”。
从一个在书店打工的女孩子身上,我看到她孜孜以求的对哲学(移情主义)的迷恋,刚开始时,高级杂志社要拍几组时装照到书店取景,她十分厌恶这帮人,也压根儿没想讨好他们,也许是这种个性让摄影师注意到她,并将她作为陪衬的照片放大给编辑看。时尚界更迭极速,不再执著于表现“胸大无脑”的美女,而开始讨好起赫本这样集智慧与美貌于一体的美女。恰巧她正打算攒钱去巴黎听移情主义教授的讲演,被拉去做了模特儿,利用这种职务之便,她在巴黎终于遇到了梦昩以求的哲学大师……然而,她同样遇到了难题:是选择继续当模特儿还是追随大师,当然是后者——她的任性没有实现她的理想,却成就她一段美好的姻缘。
在片中,奥黛丽·赫本与弗雷德有精彩的舞蹈表演:灯光昏暗的酒吧,猫一样腰肢伸展的她与舞者动作合一、畅快淋漓的跳跃着;公寓楼下路灯斜照的马路上,他斗牛士般火热、澎湃的舞姿引得女孩连连鼓掌叫好。奥黛丽在该片中没有突破她的演技,却很好的利用了一下舞蹈基础——之前,她被法国小说家克莱特(Colette)相中出演舞台剧《Gigi》,并参加自己丈夫梅尔的舞台剧《Ondine》,大获好评,因此拍摄这部电影,对于已经习惯舞台表演的奥黛丽·赫本来说根本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