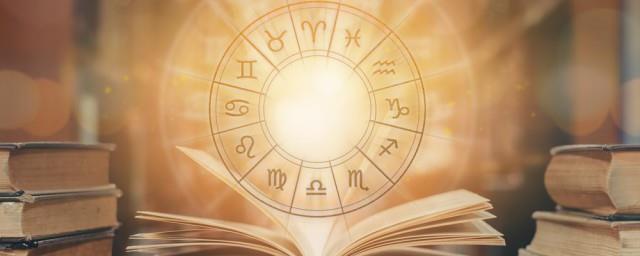1984为什么不禁?
《1984》这部文学作品,他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可能仅仅稍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很多时候真理都是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对于这部文学作品来说,也是这样。它所叙述的真理是脆弱的,也是抽象的。它在文章中虽然形成了一种让人相信的观点,但是却不能够成为打破罪恶的利器。有很多人都认为这部书应该是一部禁书,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很多人认为这部书应该是禁书也是因为这部书阐述的真理是人们无法真正握起来的。
这部文学作品只是在字里行间阐述了人间真理,可是它所阐述的这个真理是极其脆弱,一碰就碎的,也是几乎让人无法企及的。这部书没有直接涉及到现实中的罪恶,不论是哪里的作品,他们所说到的真理都是遥不可及的一个虚拟的东西,而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轻易触碰的,不论如何高尚或者怎样的低劣都是一个现实,也是往往比这些真理更加让人害怕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是人类急迫的想要解决的改善的现实社会。这部书没有涉及这些可以触碰的现实,它明明白白的只是写着真理,每个人都能够看的出来,所以不是要命的东西,因为他遥远所以变得不是那么急迫,不是那么重要。
而且作者在写这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在其中设立了一个隐形的门槛,虽然想要读得懂这部作品,不需要有多大的智慧和多么灵敏的大脑去感悟,但是也不能是一个思想太过愚钝无耻的人。大多数人可以轻易读懂这本书,但是却又不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书的内核,所以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到书中所阐释的核心,然而又要去接受这本书所描绘的理想,同样的,很多人又会对其中描述的事物有极大的抵抗心理。
正因为这部书有以上两个特点,所以它规定了限制了自己的读者群体,那些头脑过于蠢笨的人和那些不能够动用自己多重思考和接受能力的人就不能够明白这部书,也读不懂这部书。
这本书还没有成为一本禁书,也是因为很多人都不能把握这本书的内核,有一些专家做出猜测,可能是多重思想真的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这少数人很可能思想是愚钝的,很多精神病患者确实是有着让人无法琢磨的内心,可能在他们心底是比世人更加清晰的明镜,所以被大家不理解,他们或许就是那些具有多重思维的人,大多数普通的读者并不能进行把握,这部书也就因此不会成为一部禁书。
《1984》所阐述的仅仅只是真理,而真理是软弱的,是足够遥远的。真理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它可以由此形成一种坚定的信念,但无法成为一件有力的武器。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言“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所以只要不直接涉及现实,真理本身并不致命。
而人类只能无限接近却始终无法触及真理这个事实给真理烙上了不可辩驳的遥远的印记。既然是遥远的,就不是迫切的。所有要命的,都是现在的。因为所有被承认的错误必定都是已经被纠正的;所有现存的不完善都是归咎于过去的。所以如果今天的错误明天可以宣布纠正,而明天的错误又能归咎于今天,那么遥远之真理便是无足轻重的。
奥威尔狡猾地给《1984》设置了一个不易察觉的门槛。要能完全读懂《1984》即便不需要过分的聪明,但至少也不能太愚钝。当然更关键的还在于双重思想。要既能读懂它,又无法理解它。要既接受它,又坚定地拒绝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就会被它悄悄毒害和腐蚀。
因此,《1984》就幸运地免疫了这样两类可能的天敌:A.实在太笨的人;B.还不能娴熟运用双重思想的人。由此是否能得出这个推论:迄今为止,真正能够娴熟运用双重思想的家伙居然都是一些十足的蠢货?虽然这在逻辑上似乎说得通,但是我们从情感上还是很难接受的。毕竟,双重思想还是一门相当高深的学问。
《一九八四》不是没被禁过:一段时间内,它都属于“内部参考”书籍,一般人是读不到的,直到后来才逐步解禁。现在它在中国的名气太大了,如果贸然禁的话,肯定会引起巨大的骚乱(而且世界范围内,禁读《一九八四》的都是著名的极权政府)。不过到了一定时机,也不是没有被禁的可能。
很多人都会认为《1984》写得像描述中国社会,也是一党制,也是有老大哥(毛主席)光辉形象,新闻联播貌似每次都是播放着人民喜大普奔的新闻,从而认为社会主义皆不好。但我认为,如果按照《1984》所提供的假设条件,它其实并不映射中国。
因为这部电影它反映出了一个软弱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那么你才有可能有一个发言权的,要不然真的不行。
还没到禁止的时候。所述者但理,而理,懦者,为足远之。道即是一怪:其可以为一定之论,而不为一者仗,及今不直,理本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