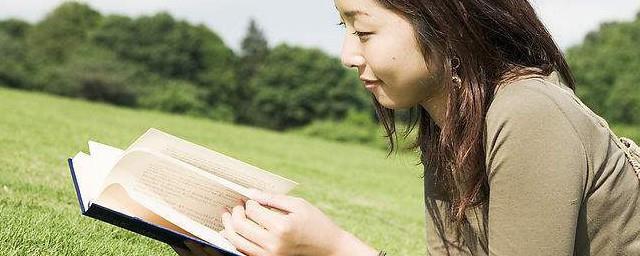小时候放寒假经常住在奶奶家,奶奶家在农村,就那种最普通的褐红色瓦房,北方的冬天很冷,奶奶就用炉子烧煤炭取暖,煤炭炉子分两层,上层放黑亮的新炭,燃烧之后逐渐崩解变成零碎的炭渣,通过两层中间的筛网落到底下一层,碳渣通常都还没完全冷却,刚落下来还是通红颜色,温度虽然赶不上上层,但也是不敢把手伸进去的,这时候奶奶就会拿来一筐自家的地瓜,也就是红薯,通过小炉门塞到底层里去,稍稍调整地瓜摆放的位置就不管它们了。等个一两个小时再打开炉门,落下的碳渣几乎把地瓜埋没了,用铁钩子把地瓜勾出来,地瓜已经被碳渣的余温焖熟,就可以吃了。这样烤出来的地瓜真的很好吃,瓜肉外焦里嫩,香甜的很。我俩就围着小炉子,奶奶边用她粗糙但灵活的手指给我扒地瓜皮,边问问我什么时候开学,要好好学习之类的、
算是一种饮料吧,我们叫doh(发音大概是这样)就是一整块冰放在那里,有人买就现场做一个碗,拿着一种类似于冰镐的东西给你碎冰,大半碗的冰搞好后,根据你的口味加酸奶,如果想要甜的就给你加糖浆,然后就到了最有趣的部分:混合一般是把内容物高高甩出,再接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总是想着店家接不住会有多尴尬...还有糖粽子。粽子是很常见,但我们对粽子的吃法不一样,买两个粽子店家打开包着的草(抱歉忘了那个叫什么),把里面的糯米部分放在碟子上,用一个木锅铲一样的东西把粽子压扁,划成四到六份,浇上糖浆,给你一把叉子可以开吃了,根据口味不同一些地方还会放酸奶(说酸奶也不对,就是把酸奶放入细纱布挂起来去水分就会得到较干也比较酸的产物)。
腌雪里蕻啊。浙江一带,雪里蕻上市了,大家都会买几十上百斤屯家里腌。小时候家里有口缸,专门腌雪里蕻的。缸里放一层洗干净的菜叶子,再均匀撒一把盐,然后我爸洗好脚跳进去踩吧踩吧。直到把汁水踩出来,我妈再放一层菜一层盐。那时候我也想玩,但是我妈说只有男的能踩,女的踩了菜就变酸了?最后踩完了,用一块大石头压住。要吃的时候拿一点,可炒菜,也可下饭生吃。汁水还能炖菜。
山东杂粮大煎饼。把麦子、高梁、玉米、谷子、地瓜干等原料淘洗、浸泡,然后磨成糊状物,然后用油擦在鏊子上面擦一遍油,既去掉了鏊子上的杂物,也使得烙熟的煎饼容易与鏊子分离。当鏊子烧热以后,可以用勺子舀上一勺煎饼糊放到鏊子上,用耙子沿着鏊子摊一圈。由于鏊子是热的,煎饼糊所到之处就迅速的被凝固一层,就是所谓的煎饼。
大部分面包都是把面团高温发酵一两个小时在整形烘烤的,有些高级面包的面团需要常温发酵五六个小时或者零度左右的低温发酵一两天,然后在整形烘烤,但是这样的面包可能不适合大部分中国人的口味。
炸冰溜子。东北老菜,冬天屋檐上冻得梆硬的冰溜子,摘下来裹上面浆在油锅里炸,因为烹饪时间极短,所以在外面的面皮炸到金黄后里面的冰溜子还没有融化,趁热吃可以感受到冰火两重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