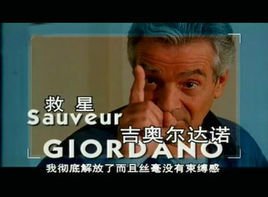电影《少女小渔》讲得是留学美国、半工半读的江伟为了能与为了他而不顾一切偷渡到纽约的小渔(刘若英饰)正式结婚,被迫策略性地先让小渔与一个失意、落寞的美国作家Mario假结婚以便拿到美国绿卡的故事。这部影片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并由李安监制、张艾嘉执导,这三个人身上的特殊气质又共同浇筑起了《少女小渔》的内核:外国人在美国的种种遭遇、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女性的自主性。
影片以移民局的突然袭击、小渔“轻车熟路”的躲避开场,刻画了“偷渡客”在美国的非法身份和无根性。他们寄居在肮脏、混乱的社会底层,为了各自的梦想而不停地消耗着美好的青春,比如江伟,比如老柴,比如那个自称来自上海的酒吧waitress;他们是漂泊在外的流浪者,默默地独自忍受冰冷的现实,比如和小渔一起工作的那些中年女工。
在禁闭了几十年的国门被渐渐打开之后,很多国人对于美国的向往绝不亚于16/17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神往。美国在他们的心中已经不是一个客观的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情感上的象征,好比当年华主席的“两个凡是”:凡是美国人的东西必定是好的;凡是有机会能够去美国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抵达梦开始的地方。于是乎,王小帅的《二弟》中的许许多多沿海民众杂糅着破釜沉舟的勇气、流离失所的伤感、幸福生活的憧憬登上了承载了太多太多的轮船,可是此轮船并不是《海上钢琴师》中的那艘一次次成功返航的大豪轮,这艘轮船经不起太平洋突如其来的海浪的侵袭,更经不起潜藏在良善外表下的人性暗淡的算计。即使他们真得到达了彼岸,可以肯定,他们的梦想又如儿时五彩缤纷的肥皂泡泡一触即破。
看过小说之后再来看电影,我又一次被深深打动。
电影一开始就带来了一抹鲜艳的红色。在昏暗的主体色调中突出红色是众多导演偏爱的一个技巧,并且一次又一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小渔并没有马上出场,首先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缝纫机下红色的布料铺陈出的氛围,随后镜头才对准了专注于工作的小渔。相对于用色彩渲染小渔的出场,马里奥的出场则用的是不同角度的镜头来表现。昏暗的赌场、百叶窗后的视线以及玻璃映照的背影,视野狭窄逼仄。这样的一组对比实则已经对人物有了一个大概的交代:小渔的单纯阳光和马里奥的困窘。严歌苓的文字是冷静简洁的,喜欢以冷酷的笔调写辛酸的现实,对旅美华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三分。电影把原著的这些元素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用细腻却不拖沓的镜头和把握得很好的节奏给观众讲故事。
小说中马里奥是极窘迫邋遢的,电影中马里奥的形象则比原著中多了分活力和玩世不恭。他和老友为数不多的几次谈话是他颓废精神状态的写照,却也透露着一丝哲学家的思辨色彩。可以说电影中,马里奥的生活被小渔带动着,因小渔的出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马里奥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小渔。马里奥的离世是故事的结尾,却也是小渔内心变化的一个高潮。最初我以为小渔这个角色不需要太多的演技,只要一种没大脑的单纯善良即可,但是刘若英最后几分钟的表演改变了我的看法。电话里江伟的催促、窗外不耐烦的汽车喇叭声以及床上奄奄一息的马里奥,这些无不牵扯着小渔的内心,刘若英并不丰富却很有层次的表情变化很完整地揭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
女性的独立自主性是张艾嘉所关注的主题之一。在杨德昌早期的电影《海滩的一天》中,张艾嘉就出色地饰演了一位由传统的家庭主妇在遭遇到婚姻问题后成长为独立自主的都市女强人的角色。而在她亲自执导的《少女小渔》中,女性(小渔)的自主性的发现就成了影片所要阐释的关键词之一了。小渔偷渡到美国纯粹是为了江伟,来到美国之后她也是唯江伟是从,在小渔的脑中根本就没有自我的概念。
Mario问她:“你为什么来美国?”小渔的回答是:“为了江伟”。但是,小渔在Mario一次次的教诲“It’s your life”,以及江伟极端自我的表现中,她慢慢地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尤其是影片的最后,在江伟的威逼、恐吓之下,她还是留在了Mario的身边,陪伴他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早晨。同时小渔看待周遭的眼神同样发生了变化:她不再低头,不再怯懦,而是异样的坚定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