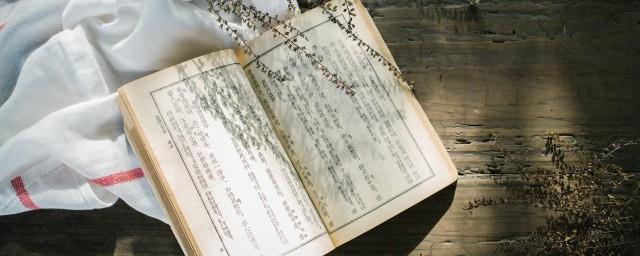我过四十不惑的年龄了。但想起小时候在农村吃过的烤红薯的味道,至今还留口水呢。我小时候,人们的生活条件还不好,红薯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主食了。每次放学后,几个小伙伴都要下地割草,好给家里的猪呀羊的吃。等太阳落山时,草也差不多割满了,几个人做个鬼脸一商量,往往要烤红薯吃。先是做下分工,有去偷红薯的,有捡柴禾的,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很快,红薯来了,柴禾有了,就要选择在哪个地方了。一是这个地方要隐蔽,免得让人发现;二是得有个高处,好挖烤红薯的坑。找好地方好,大家就齐心协力开始挖坑。坑挖好了,然后把红薯捡捡,挑那种又细又长的搭在上面,大的用铲子划开,再一层一层的摞起来。一切准备停当,划着火柴,烤红薯就开始了。一边烤,一边给红薯翻着个儿,再一边捏下红薯,看熟了没。待红薯快熟时,大家三下五除二,把红薯坑挖掉,再赶忙用土把红薯埋起来焖。大概10多分钟,再把焖过的红薯扒出来,就开始大吃一顿了。有很多时候,时间掌握的不好,或者红薯块大了,总有些半生不熟的,但大家吃起来让那么香甜。这大概是自己劳动成果的原因吧。
我不是一个吃货,但是,有一种美食让我至今想念。它就是水煎包,水煎包在当时那个年代,还是属于奢侈品的,如果你在路上碰到有人上街买早饭吃,而且吃的是水煎包,喝的是豆粥,那是非常让人羡慕,所以,曾经“吃包子喝粥”,在我们那里被认为是有钱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普通人家如果有一天能买水煎包吃,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以前在农村老家,最喜欢跟着母亲去赶集,在我们哪里,每逢阴历四八十就有集市,然后就有机会到卖水煎包的摊位看看,没准儿哪天母亲心情好,就会买一块钱的给我吃。那时候物价很便宜(这是跟现在比,当时还是觉得很贵的),一块钱能买十个水煎包,而且老板一般都会再送一个。但是,现在在我们集市上,一块钱只能买四个了,而且老板不会说再送一个,味道吃着也没有原来的好吃了。可能,我再也吃不到当年的水煎包的味道了,不是水煎包变了,是做水煎包的人变了,而且是人心变了吧。
在我们胶东,令我至今难念的美食,应该是松树蛹。胶东地处山地丘陵,漫山遍野的松树一眼望不到边。过去由于管理的不善,松树被毛虫吃的一片一片地死去。为了能尽可能的消灭毛虫,到了夏天,村里发动全村人员,拿着剪力,手上戴上用塑料包在手上的简易手套(当时没有乳胶手套),选择阴雨天,开始满山拉网式捕捉。为什么要选阴雨天呢?毛虫身上的细手,阴雨天不能沾到身上。捕捉回家后要用火烧茧皮,再用剪刀去,最后拿到深红的松虫蛹或松虫蜈蚣。这些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还要用碱水洗,待凉开后才能制作成美食。我们这里一般是油炸再撒盐或用盐水浸泡后加韭菜炒。甚是营养又美味。
我是农村长大的女汉子一枚。我小时候喜欢上山挖野菜找果子吃,也喜欢挨家挨户去蹭饭,哪家做的饭菜好吃我就去哪家,所以我最擅长找好吃的,但我最喜欢吃的是麦角,不是中药的那个麦角,是我们金华农村这边的美食,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XXL号的饺子。一张圆圆的面皮,里面放上肉馅或者素馅,然后对折,麦角就做好了。麦角要油煎的才好吃,两面都要煎成金黄色,酥酥脆脆的特好吃,但现在长大了,也忙了,很少能吃到麦角了。
在我们农村老家,有一种美食让我时刻怀念,叫薯包,吃薯包也有讲究。不怕热不上火的人出锅不久就可以尝鲜啦,咬上一口“嘎嘣”一声又香又脆;怕上火的人就得把薯包放在电饭煲的层子上蒸上一小会儿,再去品尝,还有一种独特的吃法,把煎好的薯包放进糯米自酿的酒酿里翻个身,香、甜、脆三位一体,让味蕾直呼快活!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吃法。
要说最怀念的美食,当数小时候农村过年时酥的肉了。那时候,不像现在卖东西的特别多,过年很有一种仪式感。过了腊八就是年,从这天开始,家里的父母就开始忙了,特别是过了祭灶后,整个村都在忙着蒸馍、过油。过油时,会炸不少样,比如萝卜丝、红薯丸,而令我们小孩子口馋的就是那酥的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