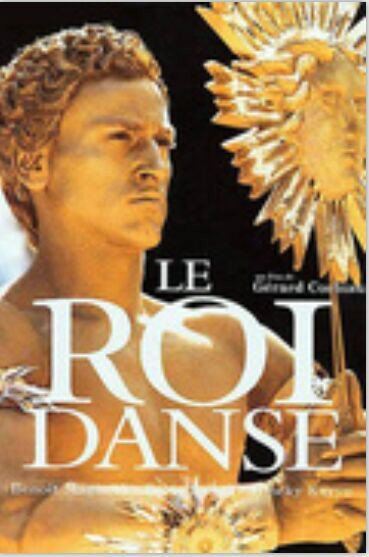《雪国》写于1935年,最初分章发表在杂志上,1937年编辑成书,但是因为川端战时一度搁笔,直到1947年,《雪国》才最终定稿。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但随之而来的评价毁誉参半,有人说是“近代文学史上抒情文学的顶峰”;但也有人评价它为“颓废和死亡的文学”。主要原因是《雪国》的主题非常隐晦,加上川端本人在文学创作上极为复杂,于是造成了如此有褒有贬的不同论调。 这部作品中最难以拿捏的角色不是驹子或叶子,反倒是男主人公岛村。岛村生活阔绰,却玩世不恭,认为一切都是徒劳,对人生持虚无态度。虽说致力于西洋舞蹈的研究,但更多是仅仅沉溺于文字和照片所虚幻出的舞蹈,并不注重现实中的舞蹈表演。同样的,面对驹子对他的爱,岛村也像对待西洋舞蹈那样缺少真情实意。所以他根本无法理解驹子对生活的憧憬和对爱情的追求。在他看来,一切都归于徒劳,他完全否定生活的价值,耽于非现实的虚幻美里无法自拔。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驹子映在镜中的美和叶子映在火车玻璃窗中的美,是虚无缥缈的非现实的美。作为一个厌世且陷于寂寞的人,岛村的排解方法是追求瞬时的官能刺激。表现就是三番几次抛下妻小与驹子幽会,满足自己对驹子的“肌肤的渴念”。但同时他也绝情地不辞而别,甚至不屑回头看一眼为他送行的驹子。同时,岛村又倾心于叶子的灵秀,川端用含蓄却又有深度的用笔描写了主人公对肉欲的追逐和对情欲的渴望。以高慧勤教授的话说,岛村仅仅追求自己的官能满足,从未把驹子看作有血有肉的人。
在《雪国》中,驹子和叶子两人,一个代表“肉”,一个代表“灵”;一个是“官能美”的体现,一个是“虚幻美”的化身。她们明知徒劳,却偏要追求生命的价值,希冀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追求超尘脱俗的境界,所以岛村感到她们的存在是那么纯真,是“纯粹的美”的化身。作家往往会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注入到作品中,所以可以说岛村的徒劳和虚无可以说是川端自己情绪的流露。川端对于岛村这样一个消极颓废的人非但没有负面化, 反倒加以美化,给他抹上一层伤感的色彩。这样一个人物既是作者自己性格的体现,也代表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阶层消极的人生态度。作者以写岛村的虚无,来反衬驹子和叶子的爱情的徒劳;通过岛村冷漠的眼睛透视驹子和叶子的形象。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穿过幽深的隧道,本来已经惊喜欢呼的“啊,这就是雪国!”却因为“夜空下一片白茫茫”情绪低转:“哦,原来已是雪国。。”川端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据说他写完一节之后,总要反复推敲琢磨,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这里不经意的笔触,隐约透出了岛村不易触动的凉薄本心,为作品定下轮廓,美丽如世外的雪国,决非现实意义的旅游胜地,而是作者幽苦悲寂的内心,寂寞寒情。以我浅薄的见识,中日文化之间存在了许多误解,最大的误会也许就是“同种同文”,一方面日本方面以为中日之间并无多少差异,了解了中国文字,彼此之间便有了同样的价值观;另一面中国人又以为日本文化源自中国,日本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附庸,就像是加拿大之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