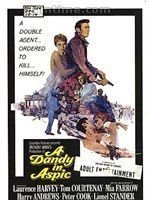年轻有为的伟同与自己的同性恋人赛门住在一所公寓里。母亲的多次“逼婚”让他焦头烂额。母亲在寄给伟同的录音带里说,她和伟同的爸爸很快就要到美国参加伟同的婚礼。无奈之下,伟同与一位租住赛门公寓的女画家微微上演了一场假结婚的闹剧。父亲因为中风住院,伟同趁机向母亲吐露了隐藏在自己心中多年的秘密——自己是个同性恋者,并嘱咐母亲不要告诉父亲。与此同时,父亲与赛门正坐在海边,平心静气的谈论着伟同与赛门之间微妙的关系。婚宴上,由于众多亲朋好友的挑唆,导致微微怀孕,赛门也因此与伟同大吵一架。打算做掉孩子的微微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决定,因为她想为孩子找到另一个父亲——赛门,赛门得知微微想让他做孩子的父亲之后,三个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回国的日子到了,伟同的父母与伟同,微微,赛门翻看着婚宴上的照片,五个人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同李安导演的《推手》相似,这部电影,继续探讨了根植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血脉之中的家庭关系,并将触角大胆的伸向了同性恋这一领域。同性恋者,直到在今天国门洞开的中国,仍然被视为一种近乎“变态”的群体。人们很难理解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遗传基因和文化密码,于是,经由同性恋造成的心理抵拒被带到了电影中,很多人在看到赛门与伟同接吻时感到不可思议,我也不例外,然而李安导演却用丰富的镜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同性恋者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赛门与伟同之间不仅仅是默契的表露,也是惺惺相惜的爱慕,是一种比异性恋更稳定,更细腻的感情。
尽管片中的主角是同性恋者,然而这部片子又不单单是讲同性恋。它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命题。热闹非凡的婚宴现场,带给众人的是开心和喜悦,而对于伟同和微微来说,却感到十分的荒唐和可笑:伟同在亲朋好友的调侃声中,很不自在的吻了新娘,而新娘的表情也很尴尬,因为他们是在表演,表演给众人看。大闹洞房那一场,几位老同学硬是要伟同和微微钻进被子里,将衣服脱光了扔出来。起先被子里没有动静,之后在老同学的逼迫下,不得已将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下,满足这些好事者的窥私欲,也为了赶紧逃脱这无聊的折腾。婚宴上折射出中国文化丑陋的痼疾,也是导演所精心设计的。
片名尽管是“喜宴”,一眼就能看出它讲的一定是充满喜感的婚宴。然而这部影片又不仅仅是在讲婚宴。他还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对于父权的抵制。片中伟同的父亲仍然是由扮演过《推手》中的父亲——郎雄先生出演。不同的是,在这部电影里,郎雄先生戴上了一副眼镜,而且从精神上看,也没有《推手》中那么矍铄。更主要的是,《推手》中展现的是儿子对于父亲的妥协,而在《喜宴》中展现的却是父亲对儿子的妥协。片中有好几个相同的场景:父亲躺倒在椅背上酣然入睡。伟同甚至以为父亲死去了,还神色紧张的凑上前去试探父亲有没有呼吸,这个场景我觉得十分好笑又倍感悲凉。最能展现父亲的妥协的那一个场景是在最后,父亲在通过机场安检时,双手举过头顶作投降状,以一个略微有些佝偻的身影背对着伟同,微微和赛门,好像向他们宣告了自己对于他们的行为的谅解,宣告了对于自己儿子的妥协,也宣告了自己的无奈与失败。
片中还有一些场景令人感到温暖,那就是伟同,微微,赛门三个人紧紧相拥在一起。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果他们是兄弟姐妹那样的关系那么人们便不太会去关注这个拥抱本身有着什么样的寓意。然而他们是这样一种奇妙的关系:伟同和赛门是同性恋人,微微是赛门和伟同的异性朋友,这样的相拥带着文化上的认可与身份上的确认:他们摒除了私心与杂念,为了一个即将出世的小生命,相互间生出了感动,在一瞬间,用一个拥抱化解了彼此的矛盾。这一刻,中国的血脉相承以一种温暖的方式浸入到赛门的个人意识中去,而微微与伟同,也因为这个小生命而达成了某种情感上的默契,三人的情感与心灵都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交融与互补。
李安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导演,这跟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很大的关联。沉着冷静细致入微扣人心弦,是他的作品呈现出来的特点。我是从《色戒》开始接触他的,当时当然是惊为天人的。后来对《色戒》又反复看了几遍 ,在不同的时间里,才发现,他(指电影)有着如梁朝伟一样深邃的眼神,一直注视着我们的内心。他反映了那么多,倾诉了那么多,好像是惊世骇俗的外表,其实是悲悯天人的内心。这就是李安,和他的电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同醇酒,越沉越美,历久弥香。
翻到《喜宴》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知道是很久之前的电影,但是看起来依旧是那么的津津有味,我几乎是第一眼就被这个镜头的运用给吸引住了。这份对男同性恋的感情的描摹,是不是就注定了李安在《断背山》上的大获成功?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在空间上,他们同处一室,在距离上,他们是咫尺之间,但是注意他们的头部的位置,仿佛真的隔着天涯隔着海在打电话。两人在神态上的痴缠打破了这上述所称的“空间距离”,非常有力的佐证了这对恋人是如此的相爱。而这种爱,是平静的,相伴在你我的身边的,并不因为他们是男同性恋而显得与众不同或是为人不堪入目。“我爱你”三个字,不再肉麻,只是一声呢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