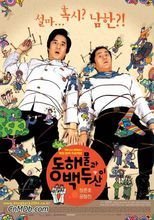白话文”与大众口语有紧密关系,“大众语不是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大众化’,即是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懂得的本领。”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就是要做‘更浅显的白话文’”。一些论者认为白话文运动是大众化运动的前奏;其实这二者的概念内涵是有区别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话文运动”等同于“大众化”。此外,白话文运动也是30年代左联时期“大众文艺”,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论起点,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与凸现,同时随之即来的是概念内涵的窄化。“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范畴确立之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争论与阐释,主要集中在“反思”层面,如钱谷融《反思白话文》等等。
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容易,可以清楚表达人们说话时的意思,而文言文,很难理解字面意思,一定要用脑筋,经过反复思考才知道所表达的意思,白话文呢,很容易表达自己所认为的东西,方便易懂。
白话文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它简练,通俗易懂。以白话文运动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对传播新思想,繁荣文学创作,推广国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
现代书面白话文语言仍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层次,一个人要参与哲学界的学术讨论必须掌握现代哲学的一整套基本话语体系,一个人要参与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必须掌握一整套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参与社会书面对话的人都必须掌握像文言文那样与自己现实日常口头语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因为现代各种不同专业的话语体系都是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这种种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也能具体运用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交流中。
古文的意义还在么?古时[六书],是为造字、用字之法,属文字学。分为象形,象声,象事,象意,转注,假借等六种。如今以口语来说,只要合音就可以了,而其他的字都可以不要了,中国文字再一演,则可演至如日本的片假名,最后也只拼音节。这个是国际潮流么?我们古人造就的文字,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后不是专家恐怕都难读解了。古文中的字都是单意字,如“五四”之后,白话文与文言文不并行,单意字演成白话文的词组,原意大多不能再解。如“变化”,原可以辩证法说理。“变”可以说是质变,忽变;“化”可以说是量变,是缓“变”。如“学习”,“学”重于思,“习”重实践,知行合一,则是学习。这些都是很好的辩证对子,而哲学翻译者却不注重这些已有的对子,另造词组,导致词不达意。古人的辩证精神很难再领略了,这此都是“五四”只重语音,不重词意之过,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并末能与西方文化契合起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私塾教育制被取消,学生不用再读[四书五经]了。此后学校中学的大部分是白话文,只有很少两篇是古文。去年高考一篇:赤兔马之死,以文言文仿[三国志]博得满分。而社会与论赞赏有之,贬斥有之。贬斥者言:都什么年代了,还提倡文言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白搞了么?又在走回头路了。
是不是进入现在文言文就不应该存在了?文言文只可供学者研究之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答的白话文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认为白话文的作用只是在普及文字上起到了一定作用。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区别不大,就是笔划简单了,如果是个读书人,简与繁的效果都差不多,不会因为繁就记不住它。白话文则是口语化了,文字与语言具有一致性。文言文则是传承而来的书面语,其特点是简明达意,不象我们说的话那样费口舌。
文言文从诞生就和古白话割裂 为了文化传播 用白话取代文言作为书面语是应该的
文言文读起来很生硬,没感情,早就该废除了!